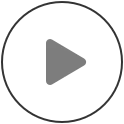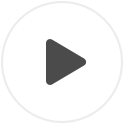反思误案:用方必察“利之弊”--葛根汤之误案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康某,黄师之师姐,吾辈以“师姑妈”称之,年已70,犹研究经方不辍。患有糖尿病、颈椎病、骨质疏松、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史。今年3月起,每夜出现发作性的单侧小腿至足址部位挛急疼痛,夜间为甚,每夜发作一两次,每次持续3至5分钟,痛甚无法入眠。曾服葛根汤及改善骨质疏松药物可缓解。近日发作又频,挛急延及双侧腓肠肌,每夜发作两三次,服用氨基葡萄糖胶囊后症状未见改善,2010年5月31日遂商治于黄师。
此本芍药甘草汤证,又伴有肩颈疼痛,故处以葛根汤加北芪,处方:北芪90克,葛根60克,麻黄10克,桂枝15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5克,生姜10克,3剂。服药后肩颈疼痛缓解,两脚挛急亦减,唯彻夜不能入睡。
6月7日,继予葛根汤剂,岂料服第1剂后,夜间双侧腓肠肌抽痛又频,足趾尤甚,每晚三四次,须不停以药油按摩方能缓解,整夜未眠,苦不堪言。且几天来又增入夜怕冷,手足凉,神疲倦怠,少气无力,腹痛,胁痛,大便溏。
6月11日,黄师意识到,此乃麻、葛更伤阳气也,即改予桂枝加附子汤,易生姜为干姜,处方:北芪60克,桂枝30克,白芍60克,赤芍30克,炙甘草30克,大枣20克,干姜20克,附子24克。4剂。服药当晚仅发作一次,甚轻,夜可安睡,次晨喜甚致电黄师。
6月15日,再与上方5剂。自后未有发作,已如常矣。
按:事后黄师坦言此案之误在于葛根汤,并谓经验与教训,尽在论中第29、30条中矣。脚挛急本是芍药甘草汤证。黄师当时觉有肩颈疼痛,加之芍药甘草汤只两味,为增其制,故投以葛根汤。服后夜不成眠,本应有所警觉,但一再误投原方,虽非“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但阳气再伤之象更为明显,故而出现肢凉畏冷、神疲乏力、便溏等。
《伤寒论》第29条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虽然此证之初并未有自汗出、小便数、心烦、恶寒等明显阳虚证,但病者素体多病,阳本不足。服葛根汤后,虽未汗出,但彻夜不眠,已提示不宜服麻黄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尚且为“误也”。夫葛根汤攻表夺阳更甚于桂枝汤,而一再投之,阳虚之证突显,脚挛急加重,为势所必然也。此时可“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然后“若厥愈足温”后,“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尤幸见阳虚之兆,即迷途知返,投以桂枝加附子汤,挽回被伤之阳。
仲景原备有三处锦囊:①第29条:“作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②第68条:“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③第30条:“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甘草干姜汤自属最轻;芍药甘草附子汤又为稍重;桂枝加附子汤更重。黄师选桂枝加附子汤且生姜易干姜,乃双管齐下,逆处求安,终归无恙。
仲景书焉可不细读乎!(若识舌象,则不会有此一误。岂可死认证乎!欲识舌象,可搜索“半百知医 中医科普之九:看舌自诊-简明舌象分类”一文。)
此本芍药甘草汤证,又伴有肩颈疼痛,故处以葛根汤加北芪,处方:北芪90克,葛根60克,麻黄10克,桂枝15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5克,生姜10克,3剂。服药后肩颈疼痛缓解,两脚挛急亦减,唯彻夜不能入睡。
6月7日,继予葛根汤剂,岂料服第1剂后,夜间双侧腓肠肌抽痛又频,足趾尤甚,每晚三四次,须不停以药油按摩方能缓解,整夜未眠,苦不堪言。且几天来又增入夜怕冷,手足凉,神疲倦怠,少气无力,腹痛,胁痛,大便溏。
6月11日,黄师意识到,此乃麻、葛更伤阳气也,即改予桂枝加附子汤,易生姜为干姜,处方:北芪60克,桂枝30克,白芍60克,赤芍30克,炙甘草30克,大枣20克,干姜20克,附子24克。4剂。服药当晚仅发作一次,甚轻,夜可安睡,次晨喜甚致电黄师。
6月15日,再与上方5剂。自后未有发作,已如常矣。
按:事后黄师坦言此案之误在于葛根汤,并谓经验与教训,尽在论中第29、30条中矣。脚挛急本是芍药甘草汤证。黄师当时觉有肩颈疼痛,加之芍药甘草汤只两味,为增其制,故投以葛根汤。服后夜不成眠,本应有所警觉,但一再误投原方,虽非“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但阳气再伤之象更为明显,故而出现肢凉畏冷、神疲乏力、便溏等。
《伤寒论》第29条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虽然此证之初并未有自汗出、小便数、心烦、恶寒等明显阳虚证,但病者素体多病,阳本不足。服葛根汤后,虽未汗出,但彻夜不眠,已提示不宜服麻黄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尚且为“误也”。夫葛根汤攻表夺阳更甚于桂枝汤,而一再投之,阳虚之证突显,脚挛急加重,为势所必然也。此时可“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然后“若厥愈足温”后,“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尤幸见阳虚之兆,即迷途知返,投以桂枝加附子汤,挽回被伤之阳。
仲景原备有三处锦囊:①第29条:“作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②第68条:“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③第30条:“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甘草干姜汤自属最轻;芍药甘草附子汤又为稍重;桂枝加附子汤更重。黄师选桂枝加附子汤且生姜易干姜,乃双管齐下,逆处求安,终归无恙。
仲景书焉可不细读乎!(若识舌象,则不会有此一误。岂可死认证乎!欲识舌象,可搜索“半百知医 中医科普之九:看舌自诊-简明舌象分类”一文。)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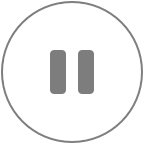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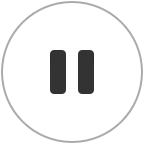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