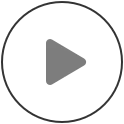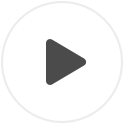临床探秘:破解千古疑难病--续命汤医案(6则)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案一:多发性硬化案。陈某,女性,39岁。2006年5月因痛失爱女悲伤欲绝,终日哭泣。2008年6月开始出现视朦,遂至眼科医院住院,诊断为“视神经炎”,治疗后双眼视力恢复同前。7月患者欲解开心结,往梧州旅游。8月6日在梧州旅游期间再次出现视朦,左下肢乏力,遂于当地医院住院。次日病情急剧加重,出现声音沙哑,四肢无力。查MR:颈3~5脊髓异常密度彩,诊断为“多发性硬化”。8月11日出现呼吸无力,诊为呼吸肌麻痹,予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当时四肢已完全不能抬离床面。8月16日转我市某三甲医院继续治疗,查脑脊液蛋白电泳,确诊为“多发性硬化”。仍以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予大剂量激素及丙种球蛋白冲击。10月12日成功脱机后,11月1日转入我院。
入院时患者精神萎靡,面色㿠白,体温:38℃左右,视物已较前清晰,呼吸稍促,气管切开,痰多,咳痰无力,四肢软瘫,双上肢可稍抬离床面,双下肢仅能床上平移,四肢惑觉障碍,颜面、脊柱及双上肢痛性痉挛,以左颈部及左上肢为甚,留置胃管、尿管,舌淡,苔簿白,脉细。中医予生脉针静滴;西医方面予抗感染、化痰,控制脊神经受累后的异常放电,并予营养支持。11月4日黄师查房。认为此为续命汤方证,故处方: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白芍60克,川芎9克,当归15克,干姜6克,炙甘草20克,桂枝10克,石膏60克,党参30克,北芪12克。
3剂后体温下降至37.5℃左右,麻黄递增至18克。7剂后,患者已无发热,精神好转,血压、心率如常,病能受药也。麻黄增至22克,佐以桂枝15克。因仍有明显痛性痉挛,加全虫10克,川足(蜈蚣)4条。10剂后,痛性痉挛明显改善,双上肢活动较前灵活。麻黄加至25克,去党参,改为高丽参30克(另炖)。患者已无明显肺部感染征象,予停用抗生素,并始予针灸、康复治疗。麻黄继续递增,最大用至30克,而未见心律失常。
12月10日,服药40天,患者精神明显好转,痰液减少,请我市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会诊,拔除气管套管,无明显痛性痉挛发作,当时已可床边小坐,双上肢活动灵活,双下肢可抬离床面。12月22日,即服药第52天,患者拔除胃管、尿管,言语清晰,自主进食,无二便失禁,可床边短距离行走,四肢感觉障碍明显减轻。
2009年1月15日,可自己步行,基本生活自理,出院。此后患者曾数次独自来我院门诊复诊,肢体活动几如常人。患者自行附近门诊康复锻炼,未再服中药。
2009年7月,患者与丈夫争吵后,出现胸闷、心悸不适,当时未见视朦及肢体麻木乏力加重。查心电图:频发室性早搏。MR:延髓及颈3脊髄内异常信号影,未排除脊髓炎。对症处理后出院。
2010年1月3日,情绪刺激及劳累后,患者再次出现右足第1、2足耻麻木、疼痛。月4日开始出现双下肢麻木。1月5日出现右下肢乏力,完全不能抬离床面,遂由家属送至广东省中医院留观,予对症处理。考虑存在频发室早,予胺碘酮口服控制心律。治疗后,下肢瘫痪症状未见好转。1月9日转神经专科治疗。1月10日开始出现左下肢乏力,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1月12日始予激素及丙种球蛋白冲击。1月17日激素减量至60mg。建议每周减10mg,减至10mg维持2周后停药。
1月22日,因上次发作服黄师所开中药后病情明显好转,故患者要求再转我院继续治疗。入院时,患者神清,视朦,声嘶,左三叉神经眼支及上颌支感觉减退,四肢肌张力齿轮样升高,双下肢乏力,左下肢肌力Ⅲ级,右下肢肌力0级,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胸10以下平面感觉减退。躯干平衡障碍,右侧肢体痉挛抽搐。心电图正常,无胸闷、心悸不适。患者停药日久,近期有室性心律失常,故师仍处以续命汤,麻黄仅予15克,并嘱注意检测心脏情况。处方如下:麻黄15克(先煎),北芪120克,桂枝30克,干姜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炙甘草30克,石膏90克。
患者服药后每日麻黄加药3克,无胸闷、心悸、汗出,三次复查心电图未见异常。至2月1日麻黄加至33克,并间断加用高丽参。患者自觉躯干平衡障碍及右侧肢体痉挛抽搐明显好转。
2月2日,患者肌力尚无明显改善,麻黄加至35克,并加细辛15克,肉桂10克。
2月4日患者双下肢肌力开始较前改善,左下肢肌力Ⅳ级,右下肢肌力Ⅰ级,声嘶亦较前好转。2月5日为加强疗效,中药改为一日两剂。病有起色,患者对黄师甚是感激,并悔当日不应过早停服中药,致病情再次加重。
2月9日患者仍有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更加白芍60克,此时患者右下肢肌力恢复至Ⅱ级,扶持下可站立。2月11日因临近春节,予带药出院,嘱门诊复诊。
2月15日患者门诊复诊,可扶行,继续服药,2周后,患者已可独立行走。
案二:多发性硬化反复发作案。赵某,女性,42岁。移居美国,1990年突发左眼失明,我市某三甲医院诊断为“多发性硬化”,激素冲击治疗后失明症状消失。但其后神经系统功能缺损症状反复发作5~6次,每次发作症状不尽相同,曾出现言语障碍、呼吸肌乏力、肢体运动障碍等表现,但每次在激素冲击后,症状均能基本缓解。末次发作于2006年,以小便失禁、双下肢截瘫为主要表现,此次经激素冲击治疗及康复治疗后,仍有明显后遗症状。双下肢萎缩,步履蹒跚,虽扶四足助行器助行,仅能行10余米,平时多坐轮椅代步。回国接受针灸治疗数月,经人介绍,于2009年5月前来请黄师诊治。患者形体纤弱,面色㿠白,舌淡,脉细。处以续命汤加北芪,麻黄用量依例逐渐递增至30克。
药后仅间有短暂心悸,余无特殊。2个月后可独立行走,精神畅旺,饮食如常。8月携黄师处方返回美国,继续服药。9月来电感觉良好,美国复诊,当地医生甚为惊讶,皆赞叹中国医学之神妙。唯麻黄一药,遍寻全城药肆均配不到,如之奈何也。2010年8月,患者回国探亲,曾多次来黄师门诊复珍,精神畅旺,可独立行走。
案三:脊髓膜瘤术后案。欧某,男性,54岁。2007年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腰痛、双下肢乏力、麻木,右下肢为主。外院予胸椎CT:相当于胸11椎体水平锥管内髄外硬膜下占位,考虑脊髓膜瘤,伴肿瘤水平以下脊髓空洞症,行手术切除。术后因“脊髓瘤术后脊髓萎缩”,在我市多家医院住院,予激素冲击、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及理疗、高压氧等治疗,效果不佳。2008年7月16日,至我院寻求中医治疗,接诊医生处以续命汤(麻黄用15克)。
7月18日,适黄师查房,见患者中等身材,形体尚壮实,然手足稍冷,右下肢痿躄,须拄杖而行,右下腹时有疼痛,按之软,大便如常,小便频而不畅,脉沉而细。黄师曰:“宜续命汤”。恰两日前我院接诊医生在场,曰已开续命汤,麻黄15克。黄师解释:“现方温经达营之剂量远未达治疗量”,书以阳和汤加减。众惊问何以用阳和汤?师曰:“阳和汤有续命意也。不过以补肾药易养血药而已”。众恍然大悟。处方:麻黄18克(先煎),肉桂10克,干姜12克,熟地30克,鹿角胶18克(烊化),北芪90克,附子30克,炙甘草30克。
麻黄用量,每两至三日递增3克,最大用至30克。患者出院后继续门诊,两月后可弃杖而行,药后稍出汗,心律如常。患者坚持门诊治疗,服用中药至今,近1年来已可独自前来复诊,行动如常人。
案四:急性胸、颈段神经根炎案。何某,男性,65岁,2008年4月18日其妻来诉,两月前始觉肢麻、头倾、乏力,在本院门诊就诊,疑为中风。自往我市某三甲医院,疑为重症肌无力,遂收入院。病情继续发展,咳逆上气,不能自主呼吸,转入ICU,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已第45天。头颅CT、MR无明显责任病灶,因病情重,未行新斯的明试验、腰穿及肌电图栓查,考虑为:急性胸、颈段神经根炎,累及呼吸肌。主管医生向其妻交代,针对病因,西医对此病无有效疗法,只能对症而已。故其妻要求自己找中医试治,获同意,故经人介绍来恳黄师往诊。
患者神识尚清,痰多,舌尖稍红,脉洪大。姑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加北芪试治。方药:北芪120克,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干姜6克,高丽参15克(炖,另兑),肉桂6克(焗),生石膏90克,甘草15克,4剂。
主管医生觉北芪、石膏太重,劝减其量,病家不以为然。师曰:此属风痱无疑,但死兆有两端:一者头倾,经云:“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一者脉洪大,重病脉大未必是安,《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曰:“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曰:“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
22日,鼻饲中药后病情稳定,按原方再进3剂。25日诊脉稍和缓,原方3剂,麻黄增至20克,再加细辛15克,嘱两味必须先煎半小时。28日往诊,白天已不用呼吸机,病者笔谈曰:“精神很好,唯入睡后怕窒息,故晚上不敢不用呼吸机”。脉象滑稍缓,微汗出,肤稍冷。
《金匮要略》原方后注:服后“汗出则愈”,佳象也。麻黄减为15克,4剂。
30日晨家属来电,昨晚停用呼吸机,一切顺利,病人安睡。
5月2日,全停呼吸机已3天,情况稳定,舌尖边略红,苔薄白,脉滑,痰多。询之有否胸翳、短气?曰:“无”。嘱病人可试坐,上方加五味子15克、枳实20克,3剂。
5月5日,呼吸机已停用第6晚,病人情况良好,自诉有些口干,舌稍红苔薄。主管医生考虑再观察三四天,便可拔除气管插管,并等待普通病房有床位,即转出ICU病房。师嘱其多坐,以渐适应日后站立行走。拟麦门冬汤加味:麦冬90克,五味子15克,高丽参15克,法夏24克,大枣20克,炙甘草24克,茯苓24克,枳实30克,北芪120克,3剂,水煎服。想麦门冬汤乃治“大逆上气,咽喉不利”。仲景描述呼吸困难一般用咳逆、气逆、喘满等,可见“大逆”非一般之上气,当是症情严重者。风痱是痿,肺痿也是痿,肺热叶焦也。再者病人今天有口干,诸症已趋稳定,麦门冬汤应合其时,仲景此方用麦冬特重--七升。
5月6日,家属来电,今天转神经内科,一切顺利,唯该科主管医生不同意外来中药,故只服了1剂。不敢有违医院制度,奈何。
5月11日,黄师往探视之,观其眼欠神,似有倦意,询之有否胸闷、呼吸急促等,自诉无不适。不便开药,唯好言以慰之。晚11时家属来电,病情急转直下,主管医生要求气管切开再上呼吸机,并谓此病不治,今后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家属不同意。
5月15日傍晚5时,家属来电,病人已转入昏迷状态。患者于5月17日死亡。
按:此例观之,乃风痱之重症,病情一度好转,又急转直下,显然与续命汤有关,莫非此方果真能续命?
案五:帕金森案。黄某,女性,51岁。素性格开朗,家庭和睦。5年前开始出现四肢乏力、僵硬,反复发热,无汗。辗转市内多家三甲医院就诊,考虑“帕金森综合征”可能性大。曾予多巴丝肼抗帕金森治疗,效果不佳。5年来病悄日益加重,逐渐出现饮水呛咳,呼吸费力,持续发热,终年无汗,卧床不起。2009年5月病情加重,高热,痰多,呼吸困难。中山一院收住院,予以气管插管,抗感染治疗,半月后生命体征较前稳定,为寻求中医治疗,经中山一院神经科主任介绍,6月11日转我院治疗。
来院时,虽神清,精神萎靡不振,经鼻气管插管,痰多,需反复吸痰,持续高热,无汗,四肢均不能抬离床面。西医治疗上以抗感染及呼吸道管理为主。中医考虑高热,无汗,予大青龙汤加减,处方:麻黄20克,桂枝15克,北杏15克,甘草15克,石膏90克,生姜12克,大枣12克。
3剂后发热未解,最高40℃,考虑病程迁延,属往来寒热,予小柴胡汤,处方:柴胡15克,黄芩25克,法夏24克,党参30克,大枣12克,生姜15克,炙甘草12克,石膏120克,麻黄6克,北杏15克。
又服3剂,仍高热,每日体温39℃,痰多,无汗。反复与家属沟通,考虑植物神经调节紊乱引起高热,建议转空调房,家属不同意,后因高热不退,转市中医院治疗。市中医院住院期间考虑感染重,痰液引流不畅,予气管切开。住院1个月,感染有所控制。家属慕黄师之名要求再转回我院寻求中药治疗。7月14日患者再次入院,此次家属同意入住空调房。入院时神疲,表情呆滞,间歇发热无汗,气管切开,痰多,四肢皆不能抬离床面。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拘急不得转侧。考虑属续命汤证,故拟方药如下:麻黄18克,北杏15克,肉桂12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2克,干姜12克,石膏60克。
2~3日麻黄递增1次,8月4日麻黄加至25克,患者精神状态较前好转,常面带微笑。8月6日患者再次出现高热不退,体温最高39℃,无汗。
又改予大青龙汤:麻黄28克,桂枝12克,北杏15克,甘草10克,石膏90克,生姜6克,大枣15克。
两日后加至麻黄30克,服药13天,仍发热,体温37~38℃,改为:麻黄30克,北杏15克,苇茎60克,薏苡仁30克,桃仁15克,石膏60克,知母15克,青天葵20克,甘草15克。
体温渐得以控制。9月1日,考虑患者体温明显下降,仍予续命汤,处方如下:麻黄33克,肉桂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5克,干姜15克,石膏60克,北芪90克。
3天后加量至35克,患者神清气爽,面带笑容,手心及腋下有微汗,吸痰次数减少,左上肢可抬离床面,双手肌力Ⅲ级以上。
按:本例患者存在两个主要汤证,其一,为续命汤证:乏力,拘急,吞咽障碍和呼吸困难。其二,为大青龙汤证:发热,无汗。因病情重,发热无汗反复出现,故在使用续命汤治疗运动障碍的同时,当发热、无汗为主要矛盾时,改予大青龙汤。
案六:胸腺瘤术后放疗后脊神经受损案。梁某,女性,48岁。康江人,粤剧名伶梁某好友。2004年因重症肌无力,查为胸腺恶性肿瘤,行胸腺手术,随之放疗,重症肌无力症状改善,但致脊神经受损,下肢行步蹒跚,麻痹不仁,全身肌肉常抽动,颈以下无汗。2008年8月因双眼睑下垂、复视,全身乏力,气短,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诊断为“重症肌无力”,用溴吡斯的明后,眼睑下垂、复视改善,但余症依然。虽出院在家,但举步维艰。
2008年10月13日经梁某介绍请吾师往视之,患者面色㿠白,带倦容,语音低微,短气眩晕,头汗涔涔,至颈而还,脉虚数。即处以《金匮要略》所附《古今录验》续命汤加味,处方:北芪120克,麻黄12克(先煎),北杏15克,白芍60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干姜10克,肉桂6克,高丽参15克(另炖),炙甘草12克,大枣15克,石膏30克。3剂。嘱服药后覆被静卧,汗出匆当风。
15日复诊,精神转佳,行路已能举步,3天来仅腓肠肌跳动一次。以前髀枢以下麻痹刺痛,现转至膝以下矣,气短改善。服药后两三个小时得汗,汗出至双臂,惟仍有眩晕,否则可以下小区花园散步矣。原方麻黄加至15克(先煎)、白芍90克、干姜15克。3剂。
18日再诊,情况良好,守方3剂。岂料19日晚来电,突然呕吐频频,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诊,诊为“重症肌无力危象”,再度入院。此后无再服中药。
2010年3月8日,患者再请黄师往诊,谓自2008年10月再进医院后,反复几次住院,双下肢活动更差,至今年春节前又突发重症肌无力危象,经抢救治疗后,主管神经科医生建议她再找中医治疗,再欲食中药云云。现常胸翳不舒,气短乏力,腹胀,双下肢不能抬离床面,只能坐轮椅,双下肢肌肉萎缩,肌肉抽搐,仍以续命汤加北芪120克,麻黄18克(先煎),每隔3天递增。至3月20日麻黄增至30克,双下肢肌肉抽搐已止,右下肢明显能自主活动,左踝也稍能摆动,胸翳憋气感觉已消失,心率:82次/分。
继续服用上方,维持麻黄用量。3月31日诉说下午双脚面、脚踝浮肿。至4月3日双脚仍浮肿,细询所服钾片(补达秀)原粒自大便排出,料是失钾所致。她咨询神经科医生,也告知是失钾,但她恐怕是中药副作用,而停用中药,奈何功败垂成也。
综上所述,《古今录验》续命汤出自《金匮要略》,原文:“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眛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组方: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各三两,川芎一两,杏仁四十枚。
上述多发性硬化案两例,第一例较重,已累及呼吸肌;第二例为典型的多发性硬化,具有时空多发性特点,发作次数多,病程较长。以上两例发病皆与感染有关,免疫机制参与,皆以累及运动系统及后组颅神经为主,伴有感觉障碍,这与续命汤原文中的症状基本相符,有是证用是方,故疗效显著。
帕金森案,除续命汤诸症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临床特点,那就是发热,这是植物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伤寒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在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下,以大青龙汤发汗退热,更为恰当。大青龙汤是麻黄汤倍麻黄,加石膏,配以姜枣组成。与续命汤相比,同是麻黄为君,桂枝辅之,只是不含川芎、当归、人参补益之药而已,其力更专。大青龙汤在发汗退热的同时,还是具有温通经隧之能的。无发热时,加上益气活血之品,就是续命汤了。
急性脊神经炎案,主要累及外周神经,是各案中病势最急、病情最重的,发病即累及呼吸肌。该患者病情危重,一度好转,中途停药,前功尽费,终至不治,奈何。
脊髓膜瘤案,为术后,又是肿瘤,阳气已虚,手足冷,小便频,故予阳和汤。黄师指出,阳和汤有续命意也,不过以补肾药易养血药而已。虽是外科名方,亦可用于此病。可见黄师用药,已臻化境。
黄师以其深厚的中医功底,对续命汤深入研究、灵活运用,取其温通宣散、益气活血之力,散血脉中凝滞之邪、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屡获奇效,以上几例验案可见一斑。故公诸同好,希望对研习经方者有所启迪。
入院时患者精神萎靡,面色㿠白,体温:38℃左右,视物已较前清晰,呼吸稍促,气管切开,痰多,咳痰无力,四肢软瘫,双上肢可稍抬离床面,双下肢仅能床上平移,四肢惑觉障碍,颜面、脊柱及双上肢痛性痉挛,以左颈部及左上肢为甚,留置胃管、尿管,舌淡,苔簿白,脉细。中医予生脉针静滴;西医方面予抗感染、化痰,控制脊神经受累后的异常放电,并予营养支持。11月4日黄师查房。认为此为续命汤方证,故处方: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白芍60克,川芎9克,当归15克,干姜6克,炙甘草20克,桂枝10克,石膏60克,党参30克,北芪12克。
3剂后体温下降至37.5℃左右,麻黄递增至18克。7剂后,患者已无发热,精神好转,血压、心率如常,病能受药也。麻黄增至22克,佐以桂枝15克。因仍有明显痛性痉挛,加全虫10克,川足(蜈蚣)4条。10剂后,痛性痉挛明显改善,双上肢活动较前灵活。麻黄加至25克,去党参,改为高丽参30克(另炖)。患者已无明显肺部感染征象,予停用抗生素,并始予针灸、康复治疗。麻黄继续递增,最大用至30克,而未见心律失常。
12月10日,服药40天,患者精神明显好转,痰液减少,请我市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会诊,拔除气管套管,无明显痛性痉挛发作,当时已可床边小坐,双上肢活动灵活,双下肢可抬离床面。12月22日,即服药第52天,患者拔除胃管、尿管,言语清晰,自主进食,无二便失禁,可床边短距离行走,四肢感觉障碍明显减轻。
2009年1月15日,可自己步行,基本生活自理,出院。此后患者曾数次独自来我院门诊复诊,肢体活动几如常人。患者自行附近门诊康复锻炼,未再服中药。
2009年7月,患者与丈夫争吵后,出现胸闷、心悸不适,当时未见视朦及肢体麻木乏力加重。查心电图:频发室性早搏。MR:延髓及颈3脊髄内异常信号影,未排除脊髓炎。对症处理后出院。
2010年1月3日,情绪刺激及劳累后,患者再次出现右足第1、2足耻麻木、疼痛。月4日开始出现双下肢麻木。1月5日出现右下肢乏力,完全不能抬离床面,遂由家属送至广东省中医院留观,予对症处理。考虑存在频发室早,予胺碘酮口服控制心律。治疗后,下肢瘫痪症状未见好转。1月9日转神经专科治疗。1月10日开始出现左下肢乏力,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1月12日始予激素及丙种球蛋白冲击。1月17日激素减量至60mg。建议每周减10mg,减至10mg维持2周后停药。
1月22日,因上次发作服黄师所开中药后病情明显好转,故患者要求再转我院继续治疗。入院时,患者神清,视朦,声嘶,左三叉神经眼支及上颌支感觉减退,四肢肌张力齿轮样升高,双下肢乏力,左下肢肌力Ⅲ级,右下肢肌力0级,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胸10以下平面感觉减退。躯干平衡障碍,右侧肢体痉挛抽搐。心电图正常,无胸闷、心悸不适。患者停药日久,近期有室性心律失常,故师仍处以续命汤,麻黄仅予15克,并嘱注意检测心脏情况。处方如下:麻黄15克(先煎),北芪120克,桂枝30克,干姜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炙甘草30克,石膏90克。
患者服药后每日麻黄加药3克,无胸闷、心悸、汗出,三次复查心电图未见异常。至2月1日麻黄加至33克,并间断加用高丽参。患者自觉躯干平衡障碍及右侧肢体痉挛抽搐明显好转。
2月2日,患者肌力尚无明显改善,麻黄加至35克,并加细辛15克,肉桂10克。
2月4日患者双下肢肌力开始较前改善,左下肢肌力Ⅳ级,右下肢肌力Ⅰ级,声嘶亦较前好转。2月5日为加强疗效,中药改为一日两剂。病有起色,患者对黄师甚是感激,并悔当日不应过早停服中药,致病情再次加重。
2月9日患者仍有肩颈及四肢肌肉僵硬,更加白芍60克,此时患者右下肢肌力恢复至Ⅱ级,扶持下可站立。2月11日因临近春节,予带药出院,嘱门诊复诊。
2月15日患者门诊复诊,可扶行,继续服药,2周后,患者已可独立行走。
案二:多发性硬化反复发作案。赵某,女性,42岁。移居美国,1990年突发左眼失明,我市某三甲医院诊断为“多发性硬化”,激素冲击治疗后失明症状消失。但其后神经系统功能缺损症状反复发作5~6次,每次发作症状不尽相同,曾出现言语障碍、呼吸肌乏力、肢体运动障碍等表现,但每次在激素冲击后,症状均能基本缓解。末次发作于2006年,以小便失禁、双下肢截瘫为主要表现,此次经激素冲击治疗及康复治疗后,仍有明显后遗症状。双下肢萎缩,步履蹒跚,虽扶四足助行器助行,仅能行10余米,平时多坐轮椅代步。回国接受针灸治疗数月,经人介绍,于2009年5月前来请黄师诊治。患者形体纤弱,面色㿠白,舌淡,脉细。处以续命汤加北芪,麻黄用量依例逐渐递增至30克。
药后仅间有短暂心悸,余无特殊。2个月后可独立行走,精神畅旺,饮食如常。8月携黄师处方返回美国,继续服药。9月来电感觉良好,美国复诊,当地医生甚为惊讶,皆赞叹中国医学之神妙。唯麻黄一药,遍寻全城药肆均配不到,如之奈何也。2010年8月,患者回国探亲,曾多次来黄师门诊复珍,精神畅旺,可独立行走。
案三:脊髓膜瘤术后案。欧某,男性,54岁。2007年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腰痛、双下肢乏力、麻木,右下肢为主。外院予胸椎CT:相当于胸11椎体水平锥管内髄外硬膜下占位,考虑脊髓膜瘤,伴肿瘤水平以下脊髓空洞症,行手术切除。术后因“脊髓瘤术后脊髓萎缩”,在我市多家医院住院,予激素冲击、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及理疗、高压氧等治疗,效果不佳。2008年7月16日,至我院寻求中医治疗,接诊医生处以续命汤(麻黄用15克)。
7月18日,适黄师查房,见患者中等身材,形体尚壮实,然手足稍冷,右下肢痿躄,须拄杖而行,右下腹时有疼痛,按之软,大便如常,小便频而不畅,脉沉而细。黄师曰:“宜续命汤”。恰两日前我院接诊医生在场,曰已开续命汤,麻黄15克。黄师解释:“现方温经达营之剂量远未达治疗量”,书以阳和汤加减。众惊问何以用阳和汤?师曰:“阳和汤有续命意也。不过以补肾药易养血药而已”。众恍然大悟。处方:麻黄18克(先煎),肉桂10克,干姜12克,熟地30克,鹿角胶18克(烊化),北芪90克,附子30克,炙甘草30克。
麻黄用量,每两至三日递增3克,最大用至30克。患者出院后继续门诊,两月后可弃杖而行,药后稍出汗,心律如常。患者坚持门诊治疗,服用中药至今,近1年来已可独自前来复诊,行动如常人。
案四:急性胸、颈段神经根炎案。何某,男性,65岁,2008年4月18日其妻来诉,两月前始觉肢麻、头倾、乏力,在本院门诊就诊,疑为中风。自往我市某三甲医院,疑为重症肌无力,遂收入院。病情继续发展,咳逆上气,不能自主呼吸,转入ICU,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已第45天。头颅CT、MR无明显责任病灶,因病情重,未行新斯的明试验、腰穿及肌电图栓查,考虑为:急性胸、颈段神经根炎,累及呼吸肌。主管医生向其妻交代,针对病因,西医对此病无有效疗法,只能对症而已。故其妻要求自己找中医试治,获同意,故经人介绍来恳黄师往诊。
患者神识尚清,痰多,舌尖稍红,脉洪大。姑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加北芪试治。方药:北芪120克,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干姜6克,高丽参15克(炖,另兑),肉桂6克(焗),生石膏90克,甘草15克,4剂。
主管医生觉北芪、石膏太重,劝减其量,病家不以为然。师曰:此属风痱无疑,但死兆有两端:一者头倾,经云:“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一者脉洪大,重病脉大未必是安,《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曰:“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曰:“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
22日,鼻饲中药后病情稳定,按原方再进3剂。25日诊脉稍和缓,原方3剂,麻黄增至20克,再加细辛15克,嘱两味必须先煎半小时。28日往诊,白天已不用呼吸机,病者笔谈曰:“精神很好,唯入睡后怕窒息,故晚上不敢不用呼吸机”。脉象滑稍缓,微汗出,肤稍冷。
《金匮要略》原方后注:服后“汗出则愈”,佳象也。麻黄减为15克,4剂。
30日晨家属来电,昨晚停用呼吸机,一切顺利,病人安睡。
5月2日,全停呼吸机已3天,情况稳定,舌尖边略红,苔薄白,脉滑,痰多。询之有否胸翳、短气?曰:“无”。嘱病人可试坐,上方加五味子15克、枳实20克,3剂。
5月5日,呼吸机已停用第6晚,病人情况良好,自诉有些口干,舌稍红苔薄。主管医生考虑再观察三四天,便可拔除气管插管,并等待普通病房有床位,即转出ICU病房。师嘱其多坐,以渐适应日后站立行走。拟麦门冬汤加味:麦冬90克,五味子15克,高丽参15克,法夏24克,大枣20克,炙甘草24克,茯苓24克,枳实30克,北芪120克,3剂,水煎服。想麦门冬汤乃治“大逆上气,咽喉不利”。仲景描述呼吸困难一般用咳逆、气逆、喘满等,可见“大逆”非一般之上气,当是症情严重者。风痱是痿,肺痿也是痿,肺热叶焦也。再者病人今天有口干,诸症已趋稳定,麦门冬汤应合其时,仲景此方用麦冬特重--七升。
5月6日,家属来电,今天转神经内科,一切顺利,唯该科主管医生不同意外来中药,故只服了1剂。不敢有违医院制度,奈何。
5月11日,黄师往探视之,观其眼欠神,似有倦意,询之有否胸闷、呼吸急促等,自诉无不适。不便开药,唯好言以慰之。晚11时家属来电,病情急转直下,主管医生要求气管切开再上呼吸机,并谓此病不治,今后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家属不同意。
5月15日傍晚5时,家属来电,病人已转入昏迷状态。患者于5月17日死亡。
按:此例观之,乃风痱之重症,病情一度好转,又急转直下,显然与续命汤有关,莫非此方果真能续命?
案五:帕金森案。黄某,女性,51岁。素性格开朗,家庭和睦。5年前开始出现四肢乏力、僵硬,反复发热,无汗。辗转市内多家三甲医院就诊,考虑“帕金森综合征”可能性大。曾予多巴丝肼抗帕金森治疗,效果不佳。5年来病悄日益加重,逐渐出现饮水呛咳,呼吸费力,持续发热,终年无汗,卧床不起。2009年5月病情加重,高热,痰多,呼吸困难。中山一院收住院,予以气管插管,抗感染治疗,半月后生命体征较前稳定,为寻求中医治疗,经中山一院神经科主任介绍,6月11日转我院治疗。
来院时,虽神清,精神萎靡不振,经鼻气管插管,痰多,需反复吸痰,持续高热,无汗,四肢均不能抬离床面。西医治疗上以抗感染及呼吸道管理为主。中医考虑高热,无汗,予大青龙汤加减,处方:麻黄20克,桂枝15克,北杏15克,甘草15克,石膏90克,生姜12克,大枣12克。
3剂后发热未解,最高40℃,考虑病程迁延,属往来寒热,予小柴胡汤,处方:柴胡15克,黄芩25克,法夏24克,党参30克,大枣12克,生姜15克,炙甘草12克,石膏120克,麻黄6克,北杏15克。
又服3剂,仍高热,每日体温39℃,痰多,无汗。反复与家属沟通,考虑植物神经调节紊乱引起高热,建议转空调房,家属不同意,后因高热不退,转市中医院治疗。市中医院住院期间考虑感染重,痰液引流不畅,予气管切开。住院1个月,感染有所控制。家属慕黄师之名要求再转回我院寻求中药治疗。7月14日患者再次入院,此次家属同意入住空调房。入院时神疲,表情呆滞,间歇发热无汗,气管切开,痰多,四肢皆不能抬离床面。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拘急不得转侧。考虑属续命汤证,故拟方药如下:麻黄18克,北杏15克,肉桂12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2克,干姜12克,石膏60克。
2~3日麻黄递增1次,8月4日麻黄加至25克,患者精神状态较前好转,常面带微笑。8月6日患者再次出现高热不退,体温最高39℃,无汗。
又改予大青龙汤:麻黄28克,桂枝12克,北杏15克,甘草10克,石膏90克,生姜6克,大枣15克。
两日后加至麻黄30克,服药13天,仍发热,体温37~38℃,改为:麻黄30克,北杏15克,苇茎60克,薏苡仁30克,桃仁15克,石膏60克,知母15克,青天葵20克,甘草15克。
体温渐得以控制。9月1日,考虑患者体温明显下降,仍予续命汤,处方如下:麻黄33克,肉桂15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党参30克,白芍60克,炙甘草30克,大枣15克,干姜15克,石膏60克,北芪90克。
3天后加量至35克,患者神清气爽,面带笑容,手心及腋下有微汗,吸痰次数减少,左上肢可抬离床面,双手肌力Ⅲ级以上。
按:本例患者存在两个主要汤证,其一,为续命汤证:乏力,拘急,吞咽障碍和呼吸困难。其二,为大青龙汤证:发热,无汗。因病情重,发热无汗反复出现,故在使用续命汤治疗运动障碍的同时,当发热、无汗为主要矛盾时,改予大青龙汤。
案六:胸腺瘤术后放疗后脊神经受损案。梁某,女性,48岁。康江人,粤剧名伶梁某好友。2004年因重症肌无力,查为胸腺恶性肿瘤,行胸腺手术,随之放疗,重症肌无力症状改善,但致脊神经受损,下肢行步蹒跚,麻痹不仁,全身肌肉常抽动,颈以下无汗。2008年8月因双眼睑下垂、复视,全身乏力,气短,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诊断为“重症肌无力”,用溴吡斯的明后,眼睑下垂、复视改善,但余症依然。虽出院在家,但举步维艰。
2008年10月13日经梁某介绍请吾师往视之,患者面色㿠白,带倦容,语音低微,短气眩晕,头汗涔涔,至颈而还,脉虚数。即处以《金匮要略》所附《古今录验》续命汤加味,处方:北芪120克,麻黄12克(先煎),北杏15克,白芍60克,川芎9克,当归24克,干姜10克,肉桂6克,高丽参15克(另炖),炙甘草12克,大枣15克,石膏30克。3剂。嘱服药后覆被静卧,汗出匆当风。
15日复诊,精神转佳,行路已能举步,3天来仅腓肠肌跳动一次。以前髀枢以下麻痹刺痛,现转至膝以下矣,气短改善。服药后两三个小时得汗,汗出至双臂,惟仍有眩晕,否则可以下小区花园散步矣。原方麻黄加至15克(先煎)、白芍90克、干姜15克。3剂。
18日再诊,情况良好,守方3剂。岂料19日晚来电,突然呕吐频频,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诊,诊为“重症肌无力危象”,再度入院。此后无再服中药。
2010年3月8日,患者再请黄师往诊,谓自2008年10月再进医院后,反复几次住院,双下肢活动更差,至今年春节前又突发重症肌无力危象,经抢救治疗后,主管神经科医生建议她再找中医治疗,再欲食中药云云。现常胸翳不舒,气短乏力,腹胀,双下肢不能抬离床面,只能坐轮椅,双下肢肌肉萎缩,肌肉抽搐,仍以续命汤加北芪120克,麻黄18克(先煎),每隔3天递增。至3月20日麻黄增至30克,双下肢肌肉抽搐已止,右下肢明显能自主活动,左踝也稍能摆动,胸翳憋气感觉已消失,心率:82次/分。
继续服用上方,维持麻黄用量。3月31日诉说下午双脚面、脚踝浮肿。至4月3日双脚仍浮肿,细询所服钾片(补达秀)原粒自大便排出,料是失钾所致。她咨询神经科医生,也告知是失钾,但她恐怕是中药副作用,而停用中药,奈何功败垂成也。
综上所述,《古今录验》续命汤出自《金匮要略》,原文:“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眛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组方: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各三两,川芎一两,杏仁四十枚。
上述多发性硬化案两例,第一例较重,已累及呼吸肌;第二例为典型的多发性硬化,具有时空多发性特点,发作次数多,病程较长。以上两例发病皆与感染有关,免疫机制参与,皆以累及运动系统及后组颅神经为主,伴有感觉障碍,这与续命汤原文中的症状基本相符,有是证用是方,故疗效显著。
帕金森案,除续命汤诸症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临床特点,那就是发热,这是植物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伤寒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在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下,以大青龙汤发汗退热,更为恰当。大青龙汤是麻黄汤倍麻黄,加石膏,配以姜枣组成。与续命汤相比,同是麻黄为君,桂枝辅之,只是不含川芎、当归、人参补益之药而已,其力更专。大青龙汤在发汗退热的同时,还是具有温通经隧之能的。无发热时,加上益气活血之品,就是续命汤了。
急性脊神经炎案,主要累及外周神经,是各案中病势最急、病情最重的,发病即累及呼吸肌。该患者病情危重,一度好转,中途停药,前功尽费,终至不治,奈何。
脊髓膜瘤案,为术后,又是肿瘤,阳气已虚,手足冷,小便频,故予阳和汤。黄师指出,阳和汤有续命意也,不过以补肾药易养血药而已。虽是外科名方,亦可用于此病。可见黄师用药,已臻化境。
黄师以其深厚的中医功底,对续命汤深入研究、灵活运用,取其温通宣散、益气活血之力,散血脉中凝滞之邪、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屡获奇效,以上几例验案可见一斑。故公诸同好,希望对研习经方者有所启迪。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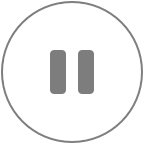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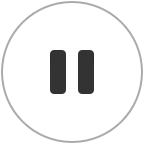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