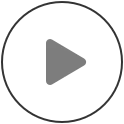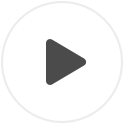在“予用之取效者屡矣”的背后--风疹头面肿痒案(两则)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案一:伍某,男性,50岁。2005年某日清晨致电吾师云:昨日全身出风团,昨晚往医院急诊,今晨未见好转,欲请师往诊。黄师即驱车前往,见头面浮肿,风团淡红,痒甚,恶风,自汗出,舌淡苔薄白。此桂枝汤证也,处方:桂枝15克,白芍15克,大枣12克,炙甘草12克,生姜3片。2剂。嘱温服,啜热粥一碗,覆被取微汗。
服1剂后,当晚瘙痒大减,次晨肿消。复诊加北芪60克,3剂。固表善后。
《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大凡表证有汗便可用桂枝汤。此例风疹初起属表无疑,自汗出便是用本方之机会。故1剂便应也。
桂枝汤乃群方之首、仲景第一方。曹颖甫曰:“予用之取效者屡矣”。其治甚广,就曹氏《经方实验录》便载六案。《吴鞠通医案·暑温门》载一自医医案,足见仲师之教,为万世法也:“丁丑六月十三日,吴,四十岁,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桂枝汤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枝八两,服半帖而愈”。有是证用是方。温病家虽暑温亦自服桂枝汤。曹氏亦谓:“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以夏令每自汗也,不拘病名,但方证对应是矣。
案二:许某,女性,45岁。某公司总会计师,因业务应酬,常啖海鲜肥厚,日前因饮花胶炖鸡汤,旋即全身皮肤现风疹块、奇痒。即往某三甲医院皮肤科诊治,诊为过敏性皮炎,该皮肤科医生本为中医,嘱咐不要用激素,先与抗过敏西药、清热疏风中药,中西药并进,1周后病情未能控制,反头面红肿更甚。遂于2010年9月15日请黄师诊治。昔日俊俏面容几难辨认,见其面部红肿,眼睑浮肿,双耳廓红肿大如梳,且皮肤脱屑,有渗出液。双手臂可见搔痒留下红肿划痕。恶风无汗,舌苔薄白,大便微溏。并诉因中秋节临近,要赴澳洲探亲,如面目全非,恐过境受阻,欲求激素控制,又相信前医告诫,不敢造次,心急如焚。黄师安慰之,先服几剂再作打算。处以甘草泻心汤加味,处方:川黄连6克,黄芩15克,干姜6克,党参30克,大枣12克,苦参15克,石膏60克,甘草30克。3剂,先泻其热,燥其湿。
9月18日复诊,红肿略消,双耳廓渗出物已干,仍痒甚。处以麻黄桂枝各半汤加味,处方: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桂枝15克,赤芍15克,大枣12克,甘草12克,石膏60克,生姜15克,生地30克。3剂,嘱温覆取微汗。
次日来电曰:“昨晚服药后,通身觉发热,约持续1个多小时,痒甚,夜不能眠”。黄师问温覆有汗否?”曰:“未有温覆”。黄师嘱曰再剂时,务必在中午12点钟前服药,且一定要温覆。
9月21日来诊曰:已温覆出汗,通体舒畅,仍有少痒,红肿消散大半,面形已复原。因明日中秋节要往澳洲探亲,望再开处方。黄师叮嘱其仍要温覆,且勿当风及日晒。仍守上方3剂。
1周后来电,肿痒基本消退。处以:生地30克,麦冬30克,知母20克,赤芍30克,甘草12克,石膏60克。7剂,水煎服。
按:黄师曰,《伤寒论》关于皮肤痒之描述但两处:一者,第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二者,在阳明篇第196条:“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其次《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治》:“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为泄风,久为痂癞…”。
综《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述,身痒之原因无非两端:一为阳明久虚,虚者阴虚也。阴虚则汗源不充,法多汗反无汗。黄师曾述当年黄继祖师公,曾治一妇人,身痒久不愈,几欲自尽,嘱以生地煲瘦肉,服之越旬而愈。此阳明久虚故也。多为身无瘾疹,但痒而已。而风邪在表不能发泄,则为最常见者。在表之邪,仍须辨有汗、无汗。有汗如例一伍姓案,自汗涔涔,此营卫不和,着眼处在汗,自是桂枝汤的证;而大多风疹身痒为无汗,如曹颖甫多用麻黄汤、麻黄加术汤,刘渡舟多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例二许姓案黄师用桂枝麻黄各半汤,皆是麻黄剂以取汗透表也。许案初服未能如法温覆,通身发热,是如仲景所言:“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也。再以白虎汤加生地、麦冬,是养阳明,清余热也。
服1剂后,当晚瘙痒大减,次晨肿消。复诊加北芪60克,3剂。固表善后。
《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大凡表证有汗便可用桂枝汤。此例风疹初起属表无疑,自汗出便是用本方之机会。故1剂便应也。
桂枝汤乃群方之首、仲景第一方。曹颖甫曰:“予用之取效者屡矣”。其治甚广,就曹氏《经方实验录》便载六案。《吴鞠通医案·暑温门》载一自医医案,足见仲师之教,为万世法也:“丁丑六月十三日,吴,四十岁,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桂枝汤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枝八两,服半帖而愈”。有是证用是方。温病家虽暑温亦自服桂枝汤。曹氏亦谓:“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以夏令每自汗也,不拘病名,但方证对应是矣。
案二:许某,女性,45岁。某公司总会计师,因业务应酬,常啖海鲜肥厚,日前因饮花胶炖鸡汤,旋即全身皮肤现风疹块、奇痒。即往某三甲医院皮肤科诊治,诊为过敏性皮炎,该皮肤科医生本为中医,嘱咐不要用激素,先与抗过敏西药、清热疏风中药,中西药并进,1周后病情未能控制,反头面红肿更甚。遂于2010年9月15日请黄师诊治。昔日俊俏面容几难辨认,见其面部红肿,眼睑浮肿,双耳廓红肿大如梳,且皮肤脱屑,有渗出液。双手臂可见搔痒留下红肿划痕。恶风无汗,舌苔薄白,大便微溏。并诉因中秋节临近,要赴澳洲探亲,如面目全非,恐过境受阻,欲求激素控制,又相信前医告诫,不敢造次,心急如焚。黄师安慰之,先服几剂再作打算。处以甘草泻心汤加味,处方:川黄连6克,黄芩15克,干姜6克,党参30克,大枣12克,苦参15克,石膏60克,甘草30克。3剂,先泻其热,燥其湿。
9月18日复诊,红肿略消,双耳廓渗出物已干,仍痒甚。处以麻黄桂枝各半汤加味,处方:麻黄15克(先煎),北杏15克,桂枝15克,赤芍15克,大枣12克,甘草12克,石膏60克,生姜15克,生地30克。3剂,嘱温覆取微汗。
次日来电曰:“昨晚服药后,通身觉发热,约持续1个多小时,痒甚,夜不能眠”。黄师问温覆有汗否?”曰:“未有温覆”。黄师嘱曰再剂时,务必在中午12点钟前服药,且一定要温覆。
9月21日来诊曰:已温覆出汗,通体舒畅,仍有少痒,红肿消散大半,面形已复原。因明日中秋节要往澳洲探亲,望再开处方。黄师叮嘱其仍要温覆,且勿当风及日晒。仍守上方3剂。
1周后来电,肿痒基本消退。处以:生地30克,麦冬30克,知母20克,赤芍30克,甘草12克,石膏60克。7剂,水煎服。
按:黄师曰,《伤寒论》关于皮肤痒之描述但两处:一者,第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二者,在阳明篇第196条:“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其次《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治》:“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为泄风,久为痂癞…”。
综《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述,身痒之原因无非两端:一为阳明久虚,虚者阴虚也。阴虚则汗源不充,法多汗反无汗。黄师曾述当年黄继祖师公,曾治一妇人,身痒久不愈,几欲自尽,嘱以生地煲瘦肉,服之越旬而愈。此阳明久虚故也。多为身无瘾疹,但痒而已。而风邪在表不能发泄,则为最常见者。在表之邪,仍须辨有汗、无汗。有汗如例一伍姓案,自汗涔涔,此营卫不和,着眼处在汗,自是桂枝汤的证;而大多风疹身痒为无汗,如曹颖甫多用麻黄汤、麻黄加术汤,刘渡舟多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例二许姓案黄师用桂枝麻黄各半汤,皆是麻黄剂以取汗透表也。许案初服未能如法温覆,通身发热,是如仲景所言:“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也。再以白虎汤加生地、麦冬,是养阳明,清余热也。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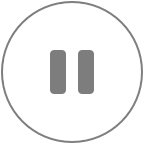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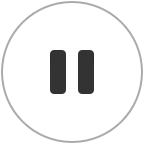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