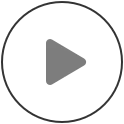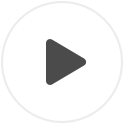详察病情,决不可为表面现象所左右--真武汤治肾衰发热案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陈某,男性,76岁。有高血压病史20余年,血压控制不佳,10年前发现高血压性肾病,未予重视。2年多前曾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3个月前病情加重,在我市某三甲医院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行血液透析治疗3次/周。20多天前因“股骨头坏死”住院,期间使用解热镇痛药物后出现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行胃大部切除术后出血止。但患者仍觉髋关节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于2009年11月7日至我院住院继续治疗。
入院时症见:精神疲锩,面色晦暗,发热,体温最高38.5℃。双髋关节疼痛,双下肢轻度浮肿。恶心,纳差,眠一般,小便量少,大便干结。予冰敷头部、腹股沟,柴胡针肌注等退热处理后效果不佳,患者仍反复发热。即查血常规:WBC:7.7×109/L,NE:74.9%,HGB:77g/L,PLT:334×109/L。尿液分析:红细胞(++),蛋白质(++),白细胞(+)。急诊生化:BUN:8.71mmol/L,CRE:793μmol/L。2009年11月8日黄师查房,见患者精神疲倦,发热,当时体温38.5℃。恶心,纳差。双下肢轻度浮肿。小便量少,大便未解。舌淡,苔白,脉沉细。本例病人,年老久病,肾衰多年,面色晦暗,小便量少,双下肢浮肿,舌淡,苔白,脉沉细,水气内结之象明显。虽发热,但无面红目赤、舌红苔黄、口渴饮冷之热象,非实热也。阳虚水泛,水郁化热,故用真武汤温阳利水,水郁解则热自退。黄师曰,此为水阻阳郁之发热。予真武汤,处方:白芍15克,熟附子15克,生姜3片,白术15克,茯苓2克。水煎内服,4剂。
药后第3天,患者发热已退,恶心减。再予上方5剂,未再发热,食欲改善,小便量增多,双下肢浮肿消退。
按:《伤寒论》第82条:“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第316条:“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对于第82条所言“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注家争论较多,其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为虚阳外浮,二为汗不如法、表证仍在。但若阳虚至汗,应急用通脉四逆汤之类回阳救逆,真武汤恐力所难及;若仍因表邪发热,焉有全不顾表而竟用真武汤之理乎?黄师认为,真武汤证之发热既非虚阳外越,亦非表邪未罢,本证之发热是水阻阳郁所致。试用仲景思想解释《伤寒论》,如以第28条为例:“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本条“仍”字提示头痛、发热、心下满诸症在汗下之前已有;亦证明汗法与下法均无效;进而证明,“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决非太阳表证,也非阳明里证。通过“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可知,本证为水气为病,水气结于心下。水气内结、里气不调而产生的肤表反应而见发热。真武汤证之发热亦类此。
黄师特别指出:临证之时,当详察病情,决不可为表面现象所左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到发热即投苦寒或解表之剂。此例个中趣味,不可不思。
入院时症见:精神疲锩,面色晦暗,发热,体温最高38.5℃。双髋关节疼痛,双下肢轻度浮肿。恶心,纳差,眠一般,小便量少,大便干结。予冰敷头部、腹股沟,柴胡针肌注等退热处理后效果不佳,患者仍反复发热。即查血常规:WBC:7.7×109/L,NE:74.9%,HGB:77g/L,PLT:334×109/L。尿液分析:红细胞(++),蛋白质(++),白细胞(+)。急诊生化:BUN:8.71mmol/L,CRE:793μmol/L。2009年11月8日黄师查房,见患者精神疲倦,发热,当时体温38.5℃。恶心,纳差。双下肢轻度浮肿。小便量少,大便未解。舌淡,苔白,脉沉细。本例病人,年老久病,肾衰多年,面色晦暗,小便量少,双下肢浮肿,舌淡,苔白,脉沉细,水气内结之象明显。虽发热,但无面红目赤、舌红苔黄、口渴饮冷之热象,非实热也。阳虚水泛,水郁化热,故用真武汤温阳利水,水郁解则热自退。黄师曰,此为水阻阳郁之发热。予真武汤,处方:白芍15克,熟附子15克,生姜3片,白术15克,茯苓2克。水煎内服,4剂。
药后第3天,患者发热已退,恶心减。再予上方5剂,未再发热,食欲改善,小便量增多,双下肢浮肿消退。
按:《伤寒论》第82条:“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第316条:“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对于第82条所言“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注家争论较多,其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为虚阳外浮,二为汗不如法、表证仍在。但若阳虚至汗,应急用通脉四逆汤之类回阳救逆,真武汤恐力所难及;若仍因表邪发热,焉有全不顾表而竟用真武汤之理乎?黄师认为,真武汤证之发热既非虚阳外越,亦非表邪未罢,本证之发热是水阻阳郁所致。试用仲景思想解释《伤寒论》,如以第28条为例:“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本条“仍”字提示头痛、发热、心下满诸症在汗下之前已有;亦证明汗法与下法均无效;进而证明,“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决非太阳表证,也非阳明里证。通过“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可知,本证为水气为病,水气结于心下。水气内结、里气不调而产生的肤表反应而见发热。真武汤证之发热亦类此。
黄师特别指出:临证之时,当详察病情,决不可为表面现象所左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到发热即投苦寒或解表之剂。此例个中趣味,不可不思。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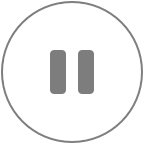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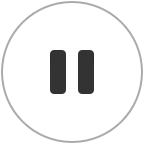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