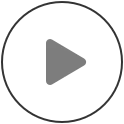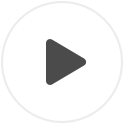经方问对之二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师:黄仕沛;徒:何莉娜)
一、六经提纲证
何莉娜:关于六经提纲证,有两个问题:
第一,小柴胡汤非专为少阳而设也。太阳篇、少阳篇、阳明篇、厥阴篇、瘥后篇均有小柴胡汤,涉及条文共20条。吴茱萸汤见于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栀子豉汤见于太阳病、阳明病、厥阴病。如此看,是否有细分六病的必要?
第二,六经提纲证能否囊括篇中所有方证?“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其实是不是所有少阴病都“脉微细,但欲寐”,这是很多人讨论过的,主要系寒化、热化的问题。热化会不会“脉微细,但欲寐”?是不是所有冠以少阴病的条文都“脉微细,但欲寐”。“阳明病,胃家实”。那么“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吴茱萸汤也是胃家实?还是,应属不能食,中寒?那么阳明病也不全是胃家实?
黄师:仲景六经非经络之六经,是从传变的角度讲,所以不应以六经视之。我意应视为六病,那么六病是否一定不与经络有关?那是用什么理论解释仲景的问题,不是仲景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内经不对,等于西医理论解释伤寒,不等于西医不对,因为病证是客观存在的,且观察的角度不同,结果规律也就不同。
六经所谓提纲,当然不是仲景语,又是伤寒学家言,不是仲景学说。我说是言其大率。即是说不能把“之为病”当代表论中所有“某某病”都具有的症状。以少阴病而言,有寒化热化,但寒化为主,故“之为病”提之。阳明病有阳明中寒,但以胃家实为主,故“之为病”乃举其要。余皆如此。六经提纲问题历来都是争议的焦点之一。除太阳病颇具纲领性外,其余都是言其大率,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非独少阳所有,阳明病条也口苦咽干。少阴病只言寒化,未言热化。余皆如此。
麻附细辛汤与四逆汤问题,前者反恶寒。后者虽踡卧,但有吐、利、肢厥、汗出…证自不同,不宜用麻黄。麻附细辛较轻浅。但按条文,仲景原意是意在解表的。现用以止痛、兴阳,是引申其义。
吴茱萸汤是厥阴篇之方。但非只用于厥阴,如“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用方问题当然是方与证的关系是关键,所以食谷欲呕,管他是阳明还是厥阴,用吴茱萸汤便是。所以八纲是关键,此汤是温药,当然不应用于热证。其实吐涎沫多已是寒,干呕,呕的时候无物,但还是口淡流涎。
二、《伤寒论》中的汗法和汗出与麻黄、桂枝、石膏
何莉娜:仲景无汗用麻黄汤,有汗用桂枝汤为定例。单从发汗力而言,麻黄汤强于桂枝汤,所以一般汗出者可耐受桂枝汤,而不能耐受麻黄汤。用麻黄汤后可用桂枝汤,而用桂枝汤后不用麻黄汤。于是,我想问,有汗是不是一定不能用麻黄汤?有汗的病人,补足液体的情况下,能否仍用麻黄汤?还是麻黄汤和桂枝汤除了发汗以外,还有其他特别的性能?
黄师:麻黄汤发汗之力强于桂枝汤是肯定的。你问:如果补足液体,是否用麻黄汤更好?我觉得:
1.中药的发汗药的药力始终不及西药,西药的发汗药从未见出现过多的、严重的副作用。我以前用大黄,你们怕泻下太过,我不是说最多就补液?麻黄剂发汗,从伤阴(失水)角度,补液当然可以。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2.中医的发汗只是表面作用,其实麻、桂、大青龙的实质作用未必在于发汗(或不只发汗)。我说麻黄汤八证有四证是疼痛,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即是说不是为发汗而发汗。要发汗,一粒百服灵比大青龙汤要强。同时我们临床可见,服用中药发汗药的病人也未必个个能出汗。
3.中医说汗为白血、汗为心液、汗名魄汗、为阴液、阳从汗泄……似乎汗液重要得很。其实有很多是麻黄的(副)作用。一般出汗哪会亡阳?是亡阳才表现为出汗。
何莉娜:麻黄汤与桂枝汤煎服法后均有温覆、啜粥之类,甚至有人认为发汗的是温覆、啜粥,而非麻黄汤与桂枝汤,对此您如何理解?
黄师:中药的发汗作用是肯定的,不过:①发汗的力较缓和,我觉得个体差异占比重不少。所以我用时方的话往往青蒿、香薷齐用。②中医要求不要大汗,大汗病必不除。③配合物理降温,不是指冰敷,是温覆、啜热稀粥。这又与西医冰敷作用不一,奥妙深藏,可见不是为退热而退热,不单是为退热而出汗。④由此可见,中药发汗药(方)力不及西药,但不能直观之。
何莉娜:麻黄与石膏同用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石膏能克制麻黄辛温发汗之性。就越婢汤、麻杏石甘汤而言,方中石膏用量大于麻黄,越婢汤原文有“续自汗出”,麻杏石甘汤有“汗出而喘”,能否说明此两方发汗之力不强,是因为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只要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就可以制约其辛温发汗之性?越婢汤发汗之力远逊于大青龙汤。两方比较,同样是用六两麻黄,越婢汤用半斤石膏,大青龙汤石膏如鸡子大。是因越婢汤石膏用量大,克制了麻黄,所以力弱,还是大青龙汤中有桂枝等辛温之品?而越婢汤六两麻黄同麻黄汤的三两麻黄比较又怎样?
黄师:麻黄的发汗力先取决于绝对用量和体质,然后才是配伍。桂、姜同用当然都是因素之一。但麻桂合用、麻膏合用的问题:麻桂合用不只是协同,而且是监制(我说过如果只强调协同,是只知其一)。越婢、大青龙都是六两麻黄,其发汗力后者强,当然是桂、姜的作用。至于石膏是否制约麻黄发汗问题;大青龙汤用石膏鸡子大是40~50克,当然量不及半斤之越婢。但是麻黄的绝对用量始终是首位,越婢汤我认为是发汗力强于麻黄汤,越婢以治水为主,上肿发汗,如非强力地发汗,怎能消肿(当然麻黄也有利尿作用)。大青龙汤、越婢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等用石膏都不是用以针对发热的,是针对烦躁而已,或者说使温热的药能耐受。所以相对用量对发汗与否,意义不大。
何莉娜:续命汤的问题,我们用麻黄不是因为它能发汗,但麻黄是发汗药,这是不争的事实,您一般也问病人出不出汗,证明您认为此处的麻黄虽与大剂量的石膏同用仍能发汗。那么,为什么这些病人往往无汗出?
黄师:续命汤发汗问题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常用60克石膏,哪能制约出汗?该出汗的还是要出,我发现用麻黄你想要他出汗的未必出;而想他不出汗的,却会药后出汗。所以说个体差异占第一。亡阳的病人汗出是征象,但出汗的病人一般不会致亡阳的。深圳颈椎术后头痛的病人,说他以前常常无端出汗,服用续命汤后反而不会随便出汗。出汗与否,还有一个原因,中医的发汗多是因势利导,正如姜佐景在《经方实验录》说到的:“桂枝汤必加中风证,乃得‘药汗’出,若所加者非中风证……必不得汗出,或纵出而其量必甚微,甚至不觉也。吾人既知此义,可以泛应诸汤,例如服麻黄汤而大汗出者,必其人本有麻黄汤证”。此言甚是,记得我年轻读伤寒时,想过这个问题,与同学黄某,自服大青龙汤而未见汗出。
何莉娜:虽然有汗用桂枝汤,但是桂枝汤是发汗之剂,那么此方能否止汗?(先其时发汗,则可止常自汗出。郝万山讲过的,没听过吗?)
黄师:桂枝汤能止汗,但桂枝汤毕竟是发汗之剂,不是止汗之剂。姜佐景说汗有病汗、药汗之分。《伤寒论》第21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加附子当然是止汗,仲景桂枝加芍是治腹痛,非用以止汗,芍药敛阴是注家言。但芍药也可止汗,严格讲与附子的汗不同。仲景讲及多种因发汗过多而合并大汗又出现其他情况的。例如:一者,为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一者,为大烦渴不解。一者,为发汗过多致心率失常,如桂枝甘草汤证。还有一种为:汗出而喘(第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麻杏石甘汤主之”)。再如五苓散证:第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更有一种情况是,发汗后致惊悸、奔豚的,那就可能是当时所用的发汗手段问题了。发汗不当做成变证坏证是个大课题,难以尽举……所以我认为,发汗的副作用,与病人的基础病、体质、发汗所用的药物、手段有关的。
三、下法与下利
何莉娜:阳明三急下:①目中不了了,睛不和;②发热汗多;③发汗不解,腹满痛。首先,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是怎样的症状?
黄师:我用大黄或用承气,不一定是三急下之证,多是杂病。腑实用承气的特点是痞、满、燥、实、坚。再加三急下证,急需急下存阴。留得一分津液就有一分生机。肺性脑、中风都会目中不了了(结膜水肿)。
何莉娜:是否急性脑血管意外的意识障碍、脑疝,呼衰,代谢性脑病(糖尿病酮症、低血糖昏迷、肝性脑病)等?
黄师:孤注一掷,也有逆转的机会。
何莉娜:您说的痞、满、燥、实、坚,其实就是不大便、腹满痛之类的胃肠道症状,有此就可下。而目中不了了则是像脑袋的问题,所以您说您治脑袋的问题也喜欢通腑?而所谓汗出发热只是急下存阴的预警。少阴三急下呢?咽干燥,热结旁流,腹满,真实假虚,都是急下存阴。
黄师:至于少阴三急下历来注家多有认为实乃阳明证,管他少阴不少阴。有可下之证就下。
何莉娜:大柴胡、承气、大陷胸、十枣汤如何鉴别?如果是大柴胡汤合枳术汤与大陷胸汤比较呢?
黄师:大柴胡、承气、大陷胸、十枣汤的泻下攻坚作用问题:我临床经验不足,但仅可据仲景规律去理解。答案是:其攻下作用依次排列。但仍要汤证以区别:大柴胡有往来寒热,心下满痛,痞硬。而大陷胸是按之石硬,石硬可理解为板硬,即急腹证,可参考使用。昨日一个发热,省中医门诊多天,无大热、无恶寒,胸胁微痛,腹痛,咳嗽痰血,舌苔厚腻。血常规:白细胞2.5×109/L。胸片:肺炎。我便是用大柴胡汤,他只是痞硬,不是石硬。枳术汤心下坚,大如盘,水饮所作。但大陷胸之势更急。黎庇留医案有一则产后腹大、仍如未产,日日增大,认为瘀水互结,用大陷胸汤。十枣汤以水为主,由于力最猛,故用十枣以缓之。承气以热为主,部位在腹,攻下程度最次,又强于大柴胡。各方均可泻水。以十枣、陷胸为主。
何莉娜:渴与不渴,在分辨太阴和少阴下利中真的有意义吗?
黄师: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第282条却曰:“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表面上看渴与不渴是鉴别太阴、少阴下利的指征,但不然也。
1.太阴、少阴都属其脏有寒也,都属阴。
2.不渴是正常现象,服四逆辈后出现渴也是病退的表现。
3.少阴病各条自利,均无再讲有渴。其实,阳虚阴盛不渴是正常的,而渴则是假象,虚故引水自救。是阳虚不能蒸津以上布,所以这种渴必然渴喜热饮、饮而不多,还有“小便色白者”才是“少阴病形悉具”。故此渴者,可如是看:太阴少阴同属阳虚阴盛,都可以出现不渴、或渴。临床上要辨别真渴、假渴。
何莉娜:啊,这和小青龙汤或渴,或不渴,服汤已渴者是一样的。胡老认为太阴病是阳病入阴。多死于太阴。四逆汤等方都是太阴的,是仲景故意把部分条文放在少阴篇,太阴只讲了宜服四逆辈这句。如何理解?
黄师:下利、肢冷、躁烦等危急之证当服四逆辈。但正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桂枝汤、吴茱萸汤亦散在各篇,但求方证对应,不必强求是太阴还是少阴。
四、关于小柴胡汤
何莉娜:您说,第96条所有加减法,只有柴胡、甘草没有被替换,那么半夏泻心汤是小柴胡汤去柴胡、生姜加川连、干姜。旋覆代赭汤是小柴胡去柴胡、黄芩加旋覆、代赭,这样还叫小柴胡汤的变方?当然关于半夏泻心汤,您讲过小柴胡汤误下后三个转归,一个痞,一个结胸,一个柴胡证仍在,所以泻心汤是小柴胡汤的变方。看了一篇文章《也谈经方与时方》,认为仲景方是以关键药物+药对+小方组合成的,请从这个思路解答。《也谈经方与时方》还指出,甘草泻心汤从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发展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加小半夏汤不就是半夏泻心汤了吗?后面还有一条黄连汤:“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胡希恕认为加桂枝是为了改善欲吐、气上冲等症状。我觉得半夏泻心汤更像是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黄连汤演变来的。
黄师:第96条或然证加减法,只有柴胡、甘草未换,所以主药是柴胡、甘草,这个观点是柯韵伯的,不是我的。但也有些道理。你试看,因仲景桂枝、麻黄、芍药、干姜、附子、大黄、生姜甚至桔梗等药都有与甘草配成方。且桂枝甘草汤等多成为仲景方的基方。惟柴胡剂没有基方。所以此说有一定道理。而半夏泻心汤到底由什么衍变而来?我以为可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从伤寒学来说,半夏泻心汤证(痞)的确是从小柴胡汤证误治而来,不应下而下,故而邪气内陷、正气更伤,所以治法也是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去掉解外之柴胡、生姜,保留扶正之参、枣、草。另一角度,如从方剂结构而看,半夏泻心汤可以是从甘草干姜汤、小半夏汤、三黄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汤、人参汤等方有其亲缘关系。但未必是谁由谁发展而来(甘草干姜汤之类基方除外)。
何莉娜:为什么少阳证不可汗吐下?
黄师:少阳病禁用汗吐下,论中是指出了的,如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265条:“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注家都从少阳的地位来讨论,邪在半表半里,汗、吐、下当非所宜。我说了,这个问题需要活看。
首先,小柴胡汤是不是发汗剂,注家也有不同的意见。胡希恕认为是发汗剂。我也认为小柴胡有发汗的作用。临床也发现病人服小柴胡汤后,热随汗退。论中多处都提及本方的发汗作用。例如本方或然证加减法中有加桂枝并温覆取汗的。当然,是说“外有微热”时用的。又有柴胡桂枝汤。虽然,都是加了桂枝。但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虽说是战汗自解,但此时的战汗毕竟是“复与柴胡汤”后才出现的。
同时,我分析,仲景告诫的误汗,可能其中有部分是指当时流行的烧针、温针等强发其汗的方法。不特少阳不宜,太阳也不宜的,如117条:“烧针令汗出,核起而赤,必发奔豚”;118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牡汤主之”。221条:“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第7条更是:“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267条:“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我说过,当时的烧针、温针、火熏等都是很野蛮的治疗手段,引起病者恐惧,故而造成奔豚、惊痫、瘛疭、怵惕、烦躁等神经精神症状。仲景屡屡反对。这也是仲景比《内经》及当时的医疗水平进步之处。不是少阳的问题,是治疗手段的问题。犹如“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此心悸是麻黄的副作用引至而非发汗手段引至同理。因此,像149条用小柴胡汤后“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笞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都是服了小柴胡汤后汗出而解的。证之临床,柴胡退热是通过出汗而退的。上述两条虽是阳明病,但若在少阳病用了小柴胡不是同样汗出吗?这样的发汗方法是不禁的,禁的是强发其汗的温针、烧针、火熏等发汗方法。《经方实验录》姜佐景有一段话,看起来与我的意思暗合,他在奔豚周案后按语中说:“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必发奔豚”。试问烧针令汗,何故多发奔豚?历来注家少有善解。不知仲景早经自作注释,曰“加温针,必惊也”;曰:“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曰:“奔豚…皆从惊恐得之”。合而观之,则烧针所以发奔豚之理宁非至明?故以经解经,反胜赘说多多,
下法也是,汉朝习惯以“丸药下之”。丸药是猛烈的泻下剂。仲景往往忌的也是此等方法,少阳病若有该下指征时还是可以下,如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等。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正如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潮热等里有实证,本来是要下法的,但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吐法,其应用范围更少。少阳病何必用吐法?
何莉娜:第204条说:“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呕多,即是少阳?所以不可攻之?少阳有呕,呕不一定是少阳。你不是说第377条至381条是鉴别呕的吗?呕多又有阳明证,如果是腑实,如肠梗阻的呕呢?如同我那天看的那个不完全性肠梗阻,呕不能食的住院病人。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合小承气汤,最后腑气通了,呕随之止了。如果理解为像第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只有这样的呕才不能吐下?因为这个是明显的柴胡证,当然要用柴胡汤,所谓不可吐下,只要方证对应,不用其他不对应的方的意思吧?该吐下还是得吐下。
黄师:“呕多,即是少阳”。不能这么说。伤寒论言呕的条文共50多条,少阳多呕。成无己说:“半表半里证,多云呕也”。204条:“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如上说伤寒呕多,共有50多条条文,而大多注家认为病势趋上,所以虽有阳明证,也不宜孟浪攻之。但曹颖甫的意思是“呕多”不等于“多呕应先治其呕,他举了三个病例:一个是腹满而“哕”的,下后呃不止,二日后死。一个是十五日不大便,终日呕吐…以其不能进药,先用吴萸三钱,煎好先服,继用大承气汤一剂愈。另一例也同法,是呕可下的活例。第一例“哕”则是胃气败。但要注意,不等于下法便是攻下,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也不算攻。如250条“与小承气汤和之愈”。251条:“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和之…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即是说,有可下的仍要下,但是掌握下的分寸,以免徒伤胃气、津液。如《金匮要略》大黄甘草汤“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我也曾用此方治过一例不完全性肠梗阻,便通呕便止。
何莉娜:关于鉴别呕:
1.第377条四逆汤的呕,未见过,您认为是否似传染病之类?
2.第378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第243条:“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第309条:“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一条在厥阴,一条在阳明,一条在少阴。其实讲的都是同一种呕--吴茱萸汤的呕,对吧?
3.呕而发热都不一定是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伤寒论》中呕和发热并见的还有真武汤,所以也可能是真武汤证,对吧?
黄师:关于呕的鉴别,如上说,伤寒论关于呕吐的条文共50多条,涉及三阳、三阴各篇。各证鉴别,难一一尽述。病机总不外乎胃气上逆。具体治法也是和胃止呕为主,如半夏、生姜、吴茱萸等,结合各病情施治。四逆汤之呕,是否传染病很难说。如霍乱便是传染病。各条吴茱萸汤当然都是一样寒邪犯胃。呕而发热以大、小柴胡为主。真武汤之热多是微热,不会如大小柴胡之热,呕是或然证,未必与发热同见。
何莉娜:《伤寒论》关于小柴胡汤的有潮热的条文有三条,我们的丑夜发热案您曾提及,日晡潮热的只有柴胡加芒硝汤、大承气汤、大陷胸汤三条,意思即是虽然潮热主要是承气汤,往来寒热主要是小柴胡汤,但是都不是绝对。其实所谓一证便是,也是要辩证地看,不能呕就用柴胡汤,潮热就承气汤。
黄师:何谓潮热,历来有三种诠释:①如潮涌一样,一阵一阵。②潮湿之意,伴有微汗出。③如成无己所谓:“若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潮热属阳明,必于日晡时发乃为潮热”。三种途释可备作参考。
看论中“潮热”一词,共出现12次,日晡所潮热仅出现3次,除104条外,还有137条、212条。其余均未说日晡所发,即未必是日晡所发,亦即其来不失其时,便可称潮热。而且208条:“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不要断章取义,以为潮热一定便是承气汤指征。但229条:“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还有104条、231条都是小柴胡汤证。这是潮热即发作有时之意。发作有时是小柴胡汤证之特点。
何莉娜: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此处就是半表半里的出处?我曾经问过您关于半表半里,不过还是不明白。
黄师:半表半里一词,仲景原文并无表述,是成无己的做词。原文只有这第148条“半在里半在外”。郝万山也认为不知是否成无己按此条为根据指少阳为半表半里。“半在里半在外”概念应是不同于“半表半里”的。“半表半里”是:不是表也不是里。而仲景意思是既有表证又有里证。所以仲景又说:“必有表,复有里”。自成氏之后,所有人包括近现代的中医教科书几乎无不用半表半里一词表达小柴胡汤或少阳病的机理。
关于这个问题,李心机所论甚详。他直截了当地说:“把‘半表半里’说成是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是谬误流传”。又说:“成无己的所谓‘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实际上是他的‘传经’臆说的产物”。并说:“把‘半表半里’说成来源于《伤寒论》,从而把成无己的东西强加给张仲景”。成无己“半表半里”的表达在他的《注解伤寒论》中至少出现了19次之多。可见成氏对自己之创,引以自鸣。
何莉娜:您说,小柴胡汤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对吧?您认为96条“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四个证为主干,下面各条的不同表述是上述四证的细化。加上少阳病的口苦、咽干、目眩、两耳无所闻,以及白苔、颈项强,产后篇、劳复、经水适来等情况,就是小柴胡汤的方证。说明要掌握小柴胡汤的主要的方证,但是也要知道“但见一证便是”,知常达变,才能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对吧?
黄师:小柴胡汤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和对96条的理解,实际上是其他20条围绕此条去理解。
五、半夏厚朴
汤何莉娜:您为何以半夏厚朴汤合泽泻汤治疗小儿增殖腺肥大睡眠呼吸暂停,不用葛根汤?
黄师:关于半夏厚朴汤合泽泻汤治鼻鼾、睡眠窒息,应从何说起?
1.泽泻汤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何谓支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不得卧),悬雍垂、鼻道、鼻甲等肥厚(其形如肿),此证病人多肥胖(其形如肿)。
2.咽中如有炙脔(咽中贴贴,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后世解作痰气郁结,喉部的病变。当然,此种解释,方证对应,似有点牵强,但也会取效,我试了两个,何某的外孙服了一段时期药,至今半年多未有再发啦。另一个是澳洲回来的病人,有所改善。就如甘草泻心汤日本人治精神病。又如那天我说的南海一孕妇,羊水过多,用肾着汤。其人身重,腹中如带五千钱,不就是怀孕腹过大,胎儿过长?该患者是妊娠糖尿病,羊水过多,口不渴,尿频,算不算“其人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口不渴,小便自利…腹重如带五千钱”?《内经》曰:“妇人身重,九月而瘖”。身重就是有孕(当然仲景所说的身重,未必与《内经》同)。上述自知有点牵强,仅供参考。
3.猪肤汤、桔梗汤、甘草汤、半夏散及汤、苦酒汤等均为咽喉方,可细心比较之。后两方均以半夏为主。半夏仲景都是生用,只注一洗字,即把半夏滑潺的洗去便用,对局部黏膜有刺激作用,故仲景之用量、用法也很讲究,可见半夏散及汤、苦酒汤所治不是一般的咽痛,不宜轻易用之。同时与桂枝同用,为寒证可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而半夏厚朴汤为“咽中如有炙脔”,不是如上述后两方之咽痛。加上是煎剂,现代又把半夏制到药性全无。故我用半夏厚朴汤治咽痛、咽炎时必合甘桔汤、诃黎勒散。
4.又,以半夏为主的方如大半夏汤、小半夏汤、干姜半夏散等,均以治呕为主,而不治咽喉,很多方都以小半夏汤为基础,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苓甘五味姜辛夏仁汤等,你可以比较一下半夏散及汤与小半夏汤的不同。主要是前者是散剂,要少少(含)咽之,可见是咽喉局部治疗为主。而后者是汤剂,配生姜,故以呕为主。大半夏汤之量大,配以蜜,煎煮法也奇特。所治之呕料非一般之呕。顺便一提,曹颍甫说,他用过小半夏汤治呕无效。主要是现在的半夏炮制到“本性全失”,“欲其立止呕吐,岂可得哉”。
篇后记:我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屈指已经几年,但虽读到碩士之后,对中医的认识几乎还未入门,课堂所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困惑常让人难拾信心。机缘巧合,得遇黄师后并有幸成为其门下弟子,兴奋之余心中又不免忐忑。自开始潜心研读《伤寒论》并跟随黄师出诊、录方。其提倡的“方证对应”,真正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在黄师的教导解感之下,对经方学习兴趣日浓,并渐有感悟。常电讯讨教于黄师至彻夜,自得其乐。确如黄师所言“今是而昨非”。黄师博学中医,自专攻仲景之学后,临床疗效突显,我常侍诊在侧,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黄师常教导吾辈“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犹乎段师琵琶,须不近乐器十年乃可授,防其先入为主也”(《读过伤寒论·序》语)。我自感经方学习之路虽漫漫,但终有所向,真乃此生快慰之事也。
--弟子何莉娜
一、六经提纲证
何莉娜:关于六经提纲证,有两个问题:
第一,小柴胡汤非专为少阳而设也。太阳篇、少阳篇、阳明篇、厥阴篇、瘥后篇均有小柴胡汤,涉及条文共20条。吴茱萸汤见于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栀子豉汤见于太阳病、阳明病、厥阴病。如此看,是否有细分六病的必要?
第二,六经提纲证能否囊括篇中所有方证?“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其实是不是所有少阴病都“脉微细,但欲寐”,这是很多人讨论过的,主要系寒化、热化的问题。热化会不会“脉微细,但欲寐”?是不是所有冠以少阴病的条文都“脉微细,但欲寐”。“阳明病,胃家实”。那么“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吴茱萸汤也是胃家实?还是,应属不能食,中寒?那么阳明病也不全是胃家实?
黄师:仲景六经非经络之六经,是从传变的角度讲,所以不应以六经视之。我意应视为六病,那么六病是否一定不与经络有关?那是用什么理论解释仲景的问题,不是仲景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内经不对,等于西医理论解释伤寒,不等于西医不对,因为病证是客观存在的,且观察的角度不同,结果规律也就不同。
六经所谓提纲,当然不是仲景语,又是伤寒学家言,不是仲景学说。我说是言其大率。即是说不能把“之为病”当代表论中所有“某某病”都具有的症状。以少阴病而言,有寒化热化,但寒化为主,故“之为病”提之。阳明病有阳明中寒,但以胃家实为主,故“之为病”乃举其要。余皆如此。六经提纲问题历来都是争议的焦点之一。除太阳病颇具纲领性外,其余都是言其大率,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非独少阳所有,阳明病条也口苦咽干。少阴病只言寒化,未言热化。余皆如此。
麻附细辛汤与四逆汤问题,前者反恶寒。后者虽踡卧,但有吐、利、肢厥、汗出…证自不同,不宜用麻黄。麻附细辛较轻浅。但按条文,仲景原意是意在解表的。现用以止痛、兴阳,是引申其义。
吴茱萸汤是厥阴篇之方。但非只用于厥阴,如“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用方问题当然是方与证的关系是关键,所以食谷欲呕,管他是阳明还是厥阴,用吴茱萸汤便是。所以八纲是关键,此汤是温药,当然不应用于热证。其实吐涎沫多已是寒,干呕,呕的时候无物,但还是口淡流涎。
二、《伤寒论》中的汗法和汗出与麻黄、桂枝、石膏
何莉娜:仲景无汗用麻黄汤,有汗用桂枝汤为定例。单从发汗力而言,麻黄汤强于桂枝汤,所以一般汗出者可耐受桂枝汤,而不能耐受麻黄汤。用麻黄汤后可用桂枝汤,而用桂枝汤后不用麻黄汤。于是,我想问,有汗是不是一定不能用麻黄汤?有汗的病人,补足液体的情况下,能否仍用麻黄汤?还是麻黄汤和桂枝汤除了发汗以外,还有其他特别的性能?
黄师:麻黄汤发汗之力强于桂枝汤是肯定的。你问:如果补足液体,是否用麻黄汤更好?我觉得:
1.中药的发汗药的药力始终不及西药,西药的发汗药从未见出现过多的、严重的副作用。我以前用大黄,你们怕泻下太过,我不是说最多就补液?麻黄剂发汗,从伤阴(失水)角度,补液当然可以。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2.中医的发汗只是表面作用,其实麻、桂、大青龙的实质作用未必在于发汗(或不只发汗)。我说麻黄汤八证有四证是疼痛,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即是说不是为发汗而发汗。要发汗,一粒百服灵比大青龙汤要强。同时我们临床可见,服用中药发汗药的病人也未必个个能出汗。
3.中医说汗为白血、汗为心液、汗名魄汗、为阴液、阳从汗泄……似乎汗液重要得很。其实有很多是麻黄的(副)作用。一般出汗哪会亡阳?是亡阳才表现为出汗。
何莉娜:麻黄汤与桂枝汤煎服法后均有温覆、啜粥之类,甚至有人认为发汗的是温覆、啜粥,而非麻黄汤与桂枝汤,对此您如何理解?
黄师:中药的发汗作用是肯定的,不过:①发汗的力较缓和,我觉得个体差异占比重不少。所以我用时方的话往往青蒿、香薷齐用。②中医要求不要大汗,大汗病必不除。③配合物理降温,不是指冰敷,是温覆、啜热稀粥。这又与西医冰敷作用不一,奥妙深藏,可见不是为退热而退热,不单是为退热而出汗。④由此可见,中药发汗药(方)力不及西药,但不能直观之。
何莉娜:麻黄与石膏同用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石膏能克制麻黄辛温发汗之性。就越婢汤、麻杏石甘汤而言,方中石膏用量大于麻黄,越婢汤原文有“续自汗出”,麻杏石甘汤有“汗出而喘”,能否说明此两方发汗之力不强,是因为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只要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就可以制约其辛温发汗之性?越婢汤发汗之力远逊于大青龙汤。两方比较,同样是用六两麻黄,越婢汤用半斤石膏,大青龙汤石膏如鸡子大。是因越婢汤石膏用量大,克制了麻黄,所以力弱,还是大青龙汤中有桂枝等辛温之品?而越婢汤六两麻黄同麻黄汤的三两麻黄比较又怎样?
黄师:麻黄的发汗力先取决于绝对用量和体质,然后才是配伍。桂、姜同用当然都是因素之一。但麻桂合用、麻膏合用的问题:麻桂合用不只是协同,而且是监制(我说过如果只强调协同,是只知其一)。越婢、大青龙都是六两麻黄,其发汗力后者强,当然是桂、姜的作用。至于石膏是否制约麻黄发汗问题;大青龙汤用石膏鸡子大是40~50克,当然量不及半斤之越婢。但是麻黄的绝对用量始终是首位,越婢汤我认为是发汗力强于麻黄汤,越婢以治水为主,上肿发汗,如非强力地发汗,怎能消肿(当然麻黄也有利尿作用)。大青龙汤、越婢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等用石膏都不是用以针对发热的,是针对烦躁而已,或者说使温热的药能耐受。所以相对用量对发汗与否,意义不大。
何莉娜:续命汤的问题,我们用麻黄不是因为它能发汗,但麻黄是发汗药,这是不争的事实,您一般也问病人出不出汗,证明您认为此处的麻黄虽与大剂量的石膏同用仍能发汗。那么,为什么这些病人往往无汗出?
黄师:续命汤发汗问题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常用60克石膏,哪能制约出汗?该出汗的还是要出,我发现用麻黄你想要他出汗的未必出;而想他不出汗的,却会药后出汗。所以说个体差异占第一。亡阳的病人汗出是征象,但出汗的病人一般不会致亡阳的。深圳颈椎术后头痛的病人,说他以前常常无端出汗,服用续命汤后反而不会随便出汗。出汗与否,还有一个原因,中医的发汗多是因势利导,正如姜佐景在《经方实验录》说到的:“桂枝汤必加中风证,乃得‘药汗’出,若所加者非中风证……必不得汗出,或纵出而其量必甚微,甚至不觉也。吾人既知此义,可以泛应诸汤,例如服麻黄汤而大汗出者,必其人本有麻黄汤证”。此言甚是,记得我年轻读伤寒时,想过这个问题,与同学黄某,自服大青龙汤而未见汗出。
何莉娜:虽然有汗用桂枝汤,但是桂枝汤是发汗之剂,那么此方能否止汗?(先其时发汗,则可止常自汗出。郝万山讲过的,没听过吗?)
黄师:桂枝汤能止汗,但桂枝汤毕竟是发汗之剂,不是止汗之剂。姜佐景说汗有病汗、药汗之分。《伤寒论》第21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加附子当然是止汗,仲景桂枝加芍是治腹痛,非用以止汗,芍药敛阴是注家言。但芍药也可止汗,严格讲与附子的汗不同。仲景讲及多种因发汗过多而合并大汗又出现其他情况的。例如:一者,为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一者,为大烦渴不解。一者,为发汗过多致心率失常,如桂枝甘草汤证。还有一种为:汗出而喘(第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麻杏石甘汤主之”)。再如五苓散证:第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更有一种情况是,发汗后致惊悸、奔豚的,那就可能是当时所用的发汗手段问题了。发汗不当做成变证坏证是个大课题,难以尽举……所以我认为,发汗的副作用,与病人的基础病、体质、发汗所用的药物、手段有关的。
三、下法与下利
何莉娜:阳明三急下:①目中不了了,睛不和;②发热汗多;③发汗不解,腹满痛。首先,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是怎样的症状?
黄师:我用大黄或用承气,不一定是三急下之证,多是杂病。腑实用承气的特点是痞、满、燥、实、坚。再加三急下证,急需急下存阴。留得一分津液就有一分生机。肺性脑、中风都会目中不了了(结膜水肿)。
何莉娜:是否急性脑血管意外的意识障碍、脑疝,呼衰,代谢性脑病(糖尿病酮症、低血糖昏迷、肝性脑病)等?
黄师:孤注一掷,也有逆转的机会。
何莉娜:您说的痞、满、燥、实、坚,其实就是不大便、腹满痛之类的胃肠道症状,有此就可下。而目中不了了则是像脑袋的问题,所以您说您治脑袋的问题也喜欢通腑?而所谓汗出发热只是急下存阴的预警。少阴三急下呢?咽干燥,热结旁流,腹满,真实假虚,都是急下存阴。
黄师:至于少阴三急下历来注家多有认为实乃阳明证,管他少阴不少阴。有可下之证就下。
何莉娜:大柴胡、承气、大陷胸、十枣汤如何鉴别?如果是大柴胡汤合枳术汤与大陷胸汤比较呢?
黄师:大柴胡、承气、大陷胸、十枣汤的泻下攻坚作用问题:我临床经验不足,但仅可据仲景规律去理解。答案是:其攻下作用依次排列。但仍要汤证以区别:大柴胡有往来寒热,心下满痛,痞硬。而大陷胸是按之石硬,石硬可理解为板硬,即急腹证,可参考使用。昨日一个发热,省中医门诊多天,无大热、无恶寒,胸胁微痛,腹痛,咳嗽痰血,舌苔厚腻。血常规:白细胞2.5×109/L。胸片:肺炎。我便是用大柴胡汤,他只是痞硬,不是石硬。枳术汤心下坚,大如盘,水饮所作。但大陷胸之势更急。黎庇留医案有一则产后腹大、仍如未产,日日增大,认为瘀水互结,用大陷胸汤。十枣汤以水为主,由于力最猛,故用十枣以缓之。承气以热为主,部位在腹,攻下程度最次,又强于大柴胡。各方均可泻水。以十枣、陷胸为主。
何莉娜:渴与不渴,在分辨太阴和少阴下利中真的有意义吗?
黄师: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第282条却曰:“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表面上看渴与不渴是鉴别太阴、少阴下利的指征,但不然也。
1.太阴、少阴都属其脏有寒也,都属阴。
2.不渴是正常现象,服四逆辈后出现渴也是病退的表现。
3.少阴病各条自利,均无再讲有渴。其实,阳虚阴盛不渴是正常的,而渴则是假象,虚故引水自救。是阳虚不能蒸津以上布,所以这种渴必然渴喜热饮、饮而不多,还有“小便色白者”才是“少阴病形悉具”。故此渴者,可如是看:太阴少阴同属阳虚阴盛,都可以出现不渴、或渴。临床上要辨别真渴、假渴。
何莉娜:啊,这和小青龙汤或渴,或不渴,服汤已渴者是一样的。胡老认为太阴病是阳病入阴。多死于太阴。四逆汤等方都是太阴的,是仲景故意把部分条文放在少阴篇,太阴只讲了宜服四逆辈这句。如何理解?
黄师:下利、肢冷、躁烦等危急之证当服四逆辈。但正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桂枝汤、吴茱萸汤亦散在各篇,但求方证对应,不必强求是太阴还是少阴。
四、关于小柴胡汤
何莉娜:您说,第96条所有加减法,只有柴胡、甘草没有被替换,那么半夏泻心汤是小柴胡汤去柴胡、生姜加川连、干姜。旋覆代赭汤是小柴胡去柴胡、黄芩加旋覆、代赭,这样还叫小柴胡汤的变方?当然关于半夏泻心汤,您讲过小柴胡汤误下后三个转归,一个痞,一个结胸,一个柴胡证仍在,所以泻心汤是小柴胡汤的变方。看了一篇文章《也谈经方与时方》,认为仲景方是以关键药物+药对+小方组合成的,请从这个思路解答。《也谈经方与时方》还指出,甘草泻心汤从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发展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加小半夏汤不就是半夏泻心汤了吗?后面还有一条黄连汤:“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胡希恕认为加桂枝是为了改善欲吐、气上冲等症状。我觉得半夏泻心汤更像是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黄连汤演变来的。
黄师:第96条或然证加减法,只有柴胡、甘草未换,所以主药是柴胡、甘草,这个观点是柯韵伯的,不是我的。但也有些道理。你试看,因仲景桂枝、麻黄、芍药、干姜、附子、大黄、生姜甚至桔梗等药都有与甘草配成方。且桂枝甘草汤等多成为仲景方的基方。惟柴胡剂没有基方。所以此说有一定道理。而半夏泻心汤到底由什么衍变而来?我以为可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从伤寒学来说,半夏泻心汤证(痞)的确是从小柴胡汤证误治而来,不应下而下,故而邪气内陷、正气更伤,所以治法也是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去掉解外之柴胡、生姜,保留扶正之参、枣、草。另一角度,如从方剂结构而看,半夏泻心汤可以是从甘草干姜汤、小半夏汤、三黄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汤、人参汤等方有其亲缘关系。但未必是谁由谁发展而来(甘草干姜汤之类基方除外)。
何莉娜:为什么少阳证不可汗吐下?
黄师:少阳病禁用汗吐下,论中是指出了的,如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265条:“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注家都从少阳的地位来讨论,邪在半表半里,汗、吐、下当非所宜。我说了,这个问题需要活看。
首先,小柴胡汤是不是发汗剂,注家也有不同的意见。胡希恕认为是发汗剂。我也认为小柴胡有发汗的作用。临床也发现病人服小柴胡汤后,热随汗退。论中多处都提及本方的发汗作用。例如本方或然证加减法中有加桂枝并温覆取汗的。当然,是说“外有微热”时用的。又有柴胡桂枝汤。虽然,都是加了桂枝。但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虽说是战汗自解,但此时的战汗毕竟是“复与柴胡汤”后才出现的。
同时,我分析,仲景告诫的误汗,可能其中有部分是指当时流行的烧针、温针等强发其汗的方法。不特少阳不宜,太阳也不宜的,如117条:“烧针令汗出,核起而赤,必发奔豚”;118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牡汤主之”。221条:“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第7条更是:“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267条:“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我说过,当时的烧针、温针、火熏等都是很野蛮的治疗手段,引起病者恐惧,故而造成奔豚、惊痫、瘛疭、怵惕、烦躁等神经精神症状。仲景屡屡反对。这也是仲景比《内经》及当时的医疗水平进步之处。不是少阳的问题,是治疗手段的问题。犹如“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此心悸是麻黄的副作用引至而非发汗手段引至同理。因此,像149条用小柴胡汤后“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笞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都是服了小柴胡汤后汗出而解的。证之临床,柴胡退热是通过出汗而退的。上述两条虽是阳明病,但若在少阳病用了小柴胡不是同样汗出吗?这样的发汗方法是不禁的,禁的是强发其汗的温针、烧针、火熏等发汗方法。《经方实验录》姜佐景有一段话,看起来与我的意思暗合,他在奔豚周案后按语中说:“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必发奔豚”。试问烧针令汗,何故多发奔豚?历来注家少有善解。不知仲景早经自作注释,曰“加温针,必惊也”;曰:“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曰:“奔豚…皆从惊恐得之”。合而观之,则烧针所以发奔豚之理宁非至明?故以经解经,反胜赘说多多,
下法也是,汉朝习惯以“丸药下之”。丸药是猛烈的泻下剂。仲景往往忌的也是此等方法,少阳病若有该下指征时还是可以下,如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等。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正如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潮热等里有实证,本来是要下法的,但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吐法,其应用范围更少。少阳病何必用吐法?
何莉娜:第204条说:“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呕多,即是少阳?所以不可攻之?少阳有呕,呕不一定是少阳。你不是说第377条至381条是鉴别呕的吗?呕多又有阳明证,如果是腑实,如肠梗阻的呕呢?如同我那天看的那个不完全性肠梗阻,呕不能食的住院病人。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合小承气汤,最后腑气通了,呕随之止了。如果理解为像第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只有这样的呕才不能吐下?因为这个是明显的柴胡证,当然要用柴胡汤,所谓不可吐下,只要方证对应,不用其他不对应的方的意思吧?该吐下还是得吐下。
黄师:“呕多,即是少阳”。不能这么说。伤寒论言呕的条文共50多条,少阳多呕。成无己说:“半表半里证,多云呕也”。204条:“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如上说伤寒呕多,共有50多条条文,而大多注家认为病势趋上,所以虽有阳明证,也不宜孟浪攻之。但曹颖甫的意思是“呕多”不等于“多呕应先治其呕,他举了三个病例:一个是腹满而“哕”的,下后呃不止,二日后死。一个是十五日不大便,终日呕吐…以其不能进药,先用吴萸三钱,煎好先服,继用大承气汤一剂愈。另一例也同法,是呕可下的活例。第一例“哕”则是胃气败。但要注意,不等于下法便是攻下,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也不算攻。如250条“与小承气汤和之愈”。251条:“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和之…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即是说,有可下的仍要下,但是掌握下的分寸,以免徒伤胃气、津液。如《金匮要略》大黄甘草汤“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我也曾用此方治过一例不完全性肠梗阻,便通呕便止。
何莉娜:关于鉴别呕:
1.第377条四逆汤的呕,未见过,您认为是否似传染病之类?
2.第378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第243条:“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第309条:“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一条在厥阴,一条在阳明,一条在少阴。其实讲的都是同一种呕--吴茱萸汤的呕,对吧?
3.呕而发热都不一定是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伤寒论》中呕和发热并见的还有真武汤,所以也可能是真武汤证,对吧?
黄师:关于呕的鉴别,如上说,伤寒论关于呕吐的条文共50多条,涉及三阳、三阴各篇。各证鉴别,难一一尽述。病机总不外乎胃气上逆。具体治法也是和胃止呕为主,如半夏、生姜、吴茱萸等,结合各病情施治。四逆汤之呕,是否传染病很难说。如霍乱便是传染病。各条吴茱萸汤当然都是一样寒邪犯胃。呕而发热以大、小柴胡为主。真武汤之热多是微热,不会如大小柴胡之热,呕是或然证,未必与发热同见。
何莉娜:《伤寒论》关于小柴胡汤的有潮热的条文有三条,我们的丑夜发热案您曾提及,日晡潮热的只有柴胡加芒硝汤、大承气汤、大陷胸汤三条,意思即是虽然潮热主要是承气汤,往来寒热主要是小柴胡汤,但是都不是绝对。其实所谓一证便是,也是要辩证地看,不能呕就用柴胡汤,潮热就承气汤。
黄师:何谓潮热,历来有三种诠释:①如潮涌一样,一阵一阵。②潮湿之意,伴有微汗出。③如成无己所谓:“若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潮热属阳明,必于日晡时发乃为潮热”。三种途释可备作参考。
看论中“潮热”一词,共出现12次,日晡所潮热仅出现3次,除104条外,还有137条、212条。其余均未说日晡所发,即未必是日晡所发,亦即其来不失其时,便可称潮热。而且208条:“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不要断章取义,以为潮热一定便是承气汤指征。但229条:“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还有104条、231条都是小柴胡汤证。这是潮热即发作有时之意。发作有时是小柴胡汤证之特点。
何莉娜: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此处就是半表半里的出处?我曾经问过您关于半表半里,不过还是不明白。
黄师:半表半里一词,仲景原文并无表述,是成无己的做词。原文只有这第148条“半在里半在外”。郝万山也认为不知是否成无己按此条为根据指少阳为半表半里。“半在里半在外”概念应是不同于“半表半里”的。“半表半里”是:不是表也不是里。而仲景意思是既有表证又有里证。所以仲景又说:“必有表,复有里”。自成氏之后,所有人包括近现代的中医教科书几乎无不用半表半里一词表达小柴胡汤或少阳病的机理。
关于这个问题,李心机所论甚详。他直截了当地说:“把‘半表半里’说成是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是谬误流传”。又说:“成无己的所谓‘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实际上是他的‘传经’臆说的产物”。并说:“把‘半表半里’说成来源于《伤寒论》,从而把成无己的东西强加给张仲景”。成无己“半表半里”的表达在他的《注解伤寒论》中至少出现了19次之多。可见成氏对自己之创,引以自鸣。
何莉娜:您说,小柴胡汤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对吧?您认为96条“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四个证为主干,下面各条的不同表述是上述四证的细化。加上少阳病的口苦、咽干、目眩、两耳无所闻,以及白苔、颈项强,产后篇、劳复、经水适来等情况,就是小柴胡汤的方证。说明要掌握小柴胡汤的主要的方证,但是也要知道“但见一证便是”,知常达变,才能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对吧?
黄师:小柴胡汤左右逢源,表里上下寒热进退自如,和对96条的理解,实际上是其他20条围绕此条去理解。
五、半夏厚朴
汤何莉娜:您为何以半夏厚朴汤合泽泻汤治疗小儿增殖腺肥大睡眠呼吸暂停,不用葛根汤?
黄师:关于半夏厚朴汤合泽泻汤治鼻鼾、睡眠窒息,应从何说起?
1.泽泻汤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何谓支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不得卧),悬雍垂、鼻道、鼻甲等肥厚(其形如肿),此证病人多肥胖(其形如肿)。
2.咽中如有炙脔(咽中贴贴,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后世解作痰气郁结,喉部的病变。当然,此种解释,方证对应,似有点牵强,但也会取效,我试了两个,何某的外孙服了一段时期药,至今半年多未有再发啦。另一个是澳洲回来的病人,有所改善。就如甘草泻心汤日本人治精神病。又如那天我说的南海一孕妇,羊水过多,用肾着汤。其人身重,腹中如带五千钱,不就是怀孕腹过大,胎儿过长?该患者是妊娠糖尿病,羊水过多,口不渴,尿频,算不算“其人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口不渴,小便自利…腹重如带五千钱”?《内经》曰:“妇人身重,九月而瘖”。身重就是有孕(当然仲景所说的身重,未必与《内经》同)。上述自知有点牵强,仅供参考。
3.猪肤汤、桔梗汤、甘草汤、半夏散及汤、苦酒汤等均为咽喉方,可细心比较之。后两方均以半夏为主。半夏仲景都是生用,只注一洗字,即把半夏滑潺的洗去便用,对局部黏膜有刺激作用,故仲景之用量、用法也很讲究,可见半夏散及汤、苦酒汤所治不是一般的咽痛,不宜轻易用之。同时与桂枝同用,为寒证可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而半夏厚朴汤为“咽中如有炙脔”,不是如上述后两方之咽痛。加上是煎剂,现代又把半夏制到药性全无。故我用半夏厚朴汤治咽痛、咽炎时必合甘桔汤、诃黎勒散。
4.又,以半夏为主的方如大半夏汤、小半夏汤、干姜半夏散等,均以治呕为主,而不治咽喉,很多方都以小半夏汤为基础,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苓甘五味姜辛夏仁汤等,你可以比较一下半夏散及汤与小半夏汤的不同。主要是前者是散剂,要少少(含)咽之,可见是咽喉局部治疗为主。而后者是汤剂,配生姜,故以呕为主。大半夏汤之量大,配以蜜,煎煮法也奇特。所治之呕料非一般之呕。顺便一提,曹颍甫说,他用过小半夏汤治呕无效。主要是现在的半夏炮制到“本性全失”,“欲其立止呕吐,岂可得哉”。
篇后记:我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屈指已经几年,但虽读到碩士之后,对中医的认识几乎还未入门,课堂所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困惑常让人难拾信心。机缘巧合,得遇黄师后并有幸成为其门下弟子,兴奋之余心中又不免忐忑。自开始潜心研读《伤寒论》并跟随黄师出诊、录方。其提倡的“方证对应”,真正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在黄师的教导解感之下,对经方学习兴趣日浓,并渐有感悟。常电讯讨教于黄师至彻夜,自得其乐。确如黄师所言“今是而昨非”。黄师博学中医,自专攻仲景之学后,临床疗效突显,我常侍诊在侧,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黄师常教导吾辈“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犹乎段师琵琶,须不近乐器十年乃可授,防其先入为主也”(《读过伤寒论·序》语)。我自感经方学习之路虽漫漫,但终有所向,真乃此生快慰之事也。
--弟子何莉娜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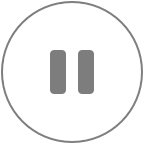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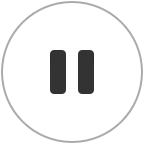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