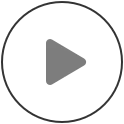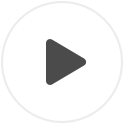不依《内经》、更非《易经》:仲景经方风格之我见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黄仕沛
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参考《汤液经法》为主,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编写成《伤寒杂病论》。其处方风格自成一派,为后世之垂范。
一、组方原则以临床为据,不依《内经》更非《易经》
自宋以后,多以《内经•至真要大论》所说为组方原则。特别近现代的教科书,更认定仲景制方是谨遵《内经》之训的。《内经•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其实无讲“佐”)。因此,解释麻黄汤为例:君--麻黄(发汗解表),臣--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佐--杏仁《助麻黄平喘),使--甘草(协和诸药)。如此解释或者可以解释麻黄汤主药次药是什么。但是否完全代表了仲景制方的原意,恐怕还是可以斟酌的。细读《伤寒论》原文便知仲景用桂枝实有监制麻黄之意,那就不是作为臣药可以解释得通的了。
《内经•至真要大论》又说:“汗者不以为奇,下者不以为偶”。但仲景峻汗之剂的“大青龙汤”却是七味药;峻下之剂“大承气汤”却是四味药。那么仲景岂非不循圣人之教,离经叛道?《内经•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在唐•王冰前是不见流传的,王冰“时于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才刊行于世。可见仲景立方之时未识本此,更遑论《汤液经》了。
至于方剂学的组成法则,把“使”药的作用强调,而有了“引经药”之说。“使”药的作用能引导君药直达病所,乃金元时期才出现的。葛根入阳明、柴胡归肝经…以及升麻升提,桔梗为舟楫之剂,诸花皆升、金石下沉等升降之说。至有把经方中难以理解的似乎便可迎刃而解了。如续命汤乃千古奇方,何以方中干姜、石膏同用?也把它诠释为痱病乃脾胃的升降失司,因而用干姜之辛温刚燥、升脾气,石膏质重而具沉降之能,所以脾胃升降功能得复,是治痱之本也。那么,“使”药便似乎成为无可替代的主药矣。难道也是仲景的原意吗?
《内经》运气七大篇,是唐代以后才介入中医学中,真正运用恐怕要更后,姑勿论运气学说的价值有多大。汉时仲景有否遵循运气、易学去制订方剂?易学医家必说是肯定的。兹录两段方解共赏。
1.五苓散。李阳波讲述、刘力红等整理的《开启中医之门•第四讲•规矩之道》中说到:“为什么它叫五苓散呢?首先运用了声韵训诂的方法,将苓训为令。令就是节令,加上一个草头,是说明植物生长与节令密切相关,一年之中,春夏秋冬长夏,也刚好是五令,这个五令又跟东南西北中,寒热温凉湿相关,因此,五苓散应该是与此相关的一个方剂。先看白术、桂枝、茯苓三味药,白术性温、桂枝性热、茯苓性平,温者东方春令之气,热者南方夏令之气,平者中央长夏之气,这里已经解决了三令,或曰三苓;还有猪苓、泽泻,按照五令五方五行的配属,北方冬令水属,水属若与动物相配,则正好与猪属相配,因此,猪苓在这里显然应该属北方冬令之气。剩下一个泽泻当然是配西方,坎离異震艮兑乾坤而配水火风雷山泽天地…其中兑泽位西,刚好与泽海相对应…五苓散的主要作用是通利水湿,而且它是分利东南西北中之湿(沛按:仲景哪条条文说五苓散治东南西北中之湿?)。当北方肾的气立出了问题而出现湿时,就应该用南方的桂枝(沛按:桂枝不是辛温吗?要辛热改附子都一样?)去对治,南方心…应用北方的猪苓(沛按:猪苓与猪有直接关系?如此说,仲景不如广东人用猪小肚(猪膀胱)煲车前草以利尿来得直接),去对治。西方…用东方白术(沛按:白术色白不是属西吗?)去对治,东方…用西方泽泻(沛按:泽漆也是泽,可以吗?)去对治,中央则用茯苓…为什么张仲景的东西这么严谨(沛按:这就叫严谨)?它已经就像我们在演算数学題目、物理题目一样”。上述一段话,也是不论正确与否,我只想问,当日仲景真是把五令故意写成五苓的吗?仲景其他方都是这样推算制订出来的吗?当然,刘教授会说仲景是这样的,如果仲景不会《易经》就当不成医圣了。
2.炙甘草汤。刘力红博士在《思考中医》317页中这样代表仲景解释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指两方的大枣数)颠倒过来?…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
好了,我不厌其烦,大篇幅引用这些论说。让大家试试,把炙甘草汤的大枣抽出五枚看这个方的功效会否质变,把当归四逆汤大枣多用五枚能否把它变成养阴方?我无心找仲景其他方反证其谬,但我坚信仲景不是根据《内经》的原则,更不是根据《易》的象数去制方的。众所周知,仲景是一个实践家、临床家(集论家,收集整理是也),因此,连处方用名都要“避道家之称”(刘教授可以说:正因为要避道家之称故把五令改五苓)。仲景制方是以临床为依据,“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我们看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35~40条。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青龙汤已下,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苓桂味甘汤”。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苓甘五味干辛汤,以治其咳满”。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苓甘五味姜辛夏汤”。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若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上述从小青龙汤加减衍变至苓甘五味姜辛夏仁大黄汤。可见仲景立方遣药有证有据,为什么小青龙汤要精简成苓桂味甘汤?为什么要去桂枝,又复加姜辛?为什么本来要用麻黄但勉用杏仁?为什么加半夏,为什么加大黄?思路讲得清清楚楚,何劳五行八卦推算一番。“读仲景书,于无字处求之”,谬也!
二、参考《汤液经法》处处紧贴临床,超越《汤液经法》
《甲乙经•序》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林亿在宋本《伤寒论》序中说:“伊尹本神农之经,仲景本汤液之法”。但是《汤液经》已不可见,其原貌怎样,无人知晓。1967年河北老中医张大昌向北京中医研究院献出古本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手抄本。自此,世人得见《汤液经》的概貌。
我们关心的是,《辅行诀》是一本什么书,以及与《伤寒论》的关系。此书卷首题曰:“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是书从《汤液经法》诸方中“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又曰:“汉晋已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佗、吴普、皇甫玄宴、支法师(引自《辅行诀》疑为支法存,晋以前名医)、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又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治疗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又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从此书可见:
1.《汤液经》一名,最早见录在《汉书•艺文志》经方类中。观陶氏所提及汉晋名医多人“咸师式此”,可见汉晋时《汤液经》尚颇流行。与《甲乙经》所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及宋•林亿所说吻合。20世纪40年代末,杨绍伊因“论广”二字疑及《伤寒论》是据《汤液经》扩充。因当时未见实物,故未引起人重视。今确信仲景乃“论广”之耳。
2.陶氏乃道家,《辅行诀》者,是辅助道士修行、“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的真“诀”(道家常用“诀”字)。但只检用常情六十首(现见仅四十六首,恐已是经后人删减),陶氏说::“《汤液经》…方亦三百六十首”。而仲景论广,只检选部分,自己增添部分。
3.“仲景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事实上,《伤寒论》之方多以某药名之,可见仲景不尚玄理、不尚浮夸,甚至形容疗效的方名都很少,不若后世什么“神效”、“仙方”等。当然现在看到的《伤寒论》尚有阳旦、青龙、白虎之名。姜春华1985年曾撰文提及“论中白虎、青龙之名犹存者,想为魏晋人依《汤液》而改”。
4.仲景根据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例如所谓二旦,即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桂枝汤,大阳旦汤即《金匮要略》黄芪建中汤,小阴旦汤即《伤寒论》黄芩汤加生姜,大阴旦汤即《伤寒论》小柴胡汤。例如《辅行诀》所载“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咽中干,每喜干呕,食不下,心中烦懑,胸胁支痛,往来寒热者方”。而到了《伤寒论》仲景则把“口苦,咽干,目眩”另立为“少阳之为病”一条,可见仲景“论”之,有了太阳、阳明、少阳之病,不再是纯方书。而小柴胡汤在《伤寒论》中有20条条文之多。可见仲景根据自己的临床所见和体会,加以“广”之。把小柴胡汤的适应证、宜忌、如何灵活运用、加减法说明,并把此方衍化成多方。淋漓尽致,理法方药皆全。又如《辅行诀》小白虎汤即《伤寒论》白虎汤,而仲景把《辅行诀》小白虎汤条文:“治天行热病,大汗出不止,口干舌燥,饮水数升不已,脉洪大者方”。改成为白虎加人参汤证,方在白虎汤中加人参。而另立白虎汤方证。如此更切合临床,层次分明。尤其是加人参,更是高明。
三、选药多自《神农本草经》,绝不芜杂
清•徐大椿曰:“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共用药物仅156味,其中《伤寒论》仅用93味,核心药物不外乎四五十味。仲景运用这些药物,巧妙组合,却足以对付临床常见病。而这93味中,载于《神农本草经》者有81味。汉时新药的发现当然不如后世之多。但是经汉前历代的经验总结,疗效肯定。再经组合,而成经典用方。
四、用药精专,甚少重叠
仲景的处方风格,不能不说其方,一证一药,甚少一证多药者,即甚少作用相同的药重叠使用。即使如“五苓散”也非如上所说“通利水湿”,如只以通利水湿,仲景是不会四味利水药齐用的。五苓散方证条文《伤寒论》、《金匮要略》共11条。归纳其证有:①“小便不利”。②“烦渴”或“汗出而渴”或“渴而口燥烦”或“微热消渴”。③“渴欲饮水,水入则吐”。④“脐下有悸”。⑤“吐涎沫而癫眩”。五类见证,其次还有“肉上粟起”等。归咎其病机为水湿内停,气化不利,津液不布。治固应利水化气。但选药却甚具针对性。简言之,五味药就是围绕上述五类症状而设的:
如“脐下有悸”--以苓桂(悸用桂或加苓,乃仲景通则)。
“癫眩”、“水入则吐”--以泽泻、白术(苦冒眩者泽泻汤主之,“冒者必呕”)。
“消渴”--以猪苓、泽泻(猪苓汤、肾气丸皆有渴,可证之)。
绝非什么春夏秋冬长夏对东南西北中,虚泛飘忽可比。亦非四苓叠用,通利水湿。尝见时人开的处方,说是用经方,每每下笔似流水,叠床架屋,动手便是十六七味。主次不明,原方影子难寻,面目全非。如某名家治咳喘,处以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姑勿论其辨证是否对应此方。仲景原方七味,尚加入紫苑、苏子、百部、前胡、黄芩、鱼腥草,共成十四味,均是清化热痰之品。可见处方之人,恐仲景方药力不逮,毫无信心,故而叠用。对自己辨证同样不自信任,心虚无定见,故而为之。
五、急、重用简
仲景方中,急重之证,药多精专。这是合情合理的:急、重之证,药少则用水少。煎煮时间不用太长,利于救治;急、重之证,药重而用宏,直达病所,解决主要矛盾。此类情况,仲景或以二三味为方,或以水二或四升,煎取一二升,采取急煎急服的办法。
第一,四逆汤类方,以回阳救逆为目的。如“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方用:附子一枚(生,破八片)、干姜一两半、甘草二两(炙)。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而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等,都是单捷小剂。即便如“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苦冒眩者,冒眩较重,不堪其苦也,用泽泻汤,以泽泻五两、白术二两。相对量重而味少,其煎法也是“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不若如炙甘草汤之“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取三升”用水、酒共十五升,则煎煮时间长矣。
第二,承气汤类急下之剂。如当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时用的大承气汤仅四味。治“胸痹”之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都是三味。治“心胸中大寒痛”之大建中汤仅三味。还有大黄附子汤等治急症之方,无不是单捷小剂。直趋病所,解决主要矛盾。
经方用量历来争议较大,由于古今度量衡差别较大,存在多种说法,近年来较权威的折算法,多依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1984年),汉一两折合今之13.92克。1995年上海柯雪帆以出土的汉代“大司农(汉代司掌度量衡的政府部门)颁的“权”进行考证,汉之一两合今之15.6克。当然,有人认为古有“神农秤”(药抨),汉之一两折合今之1~1.6克,但没有实物考证。梁•陶弘景、唐•孙思邈均未有应用。如按吴氏、柯氏的考证,对照现代一般临床医生用量,及《药典》所载用量,仲景书的用量都是相对较重的。我认为仲景书以临床为依归,所以药量较重是其风格。事实上按其用量也是较安全的。中医历来有“医者意也”、“四两拨千斤”之说法。毕竟用量太轻,是达不到治疗效果的。但近又有人把药量越用越重,附子等温热药每用750克,我认为却没有必要,观仲景温经止痛用附子量可稍大,一枚至三枚(如桂枝附子汤,三枚,炮),而温里回阳则均用一枚,通脉四逆仅大者一枚,但生用。看来是急煎,水少,急服的原因。清代广东东莞经方名医陈焕堂之《仲景归真》第一卷曰《伤寒醒俗》,意思即针砭时医之流弊,力倡仲景之正流,其中有一段提到:有人用三钱五钱生姜便谓量重,尝见广东人妇女产后,用数十斤老姜煲醋,并不觉热。我觉得他这个举例值得深思,颇具启发。①姜性虽温,但非如鸠鸩,看广东人炆鸭、炆狗肉、炆鲤鱼何不是放三五两生姜?何温之有?②凡烫姜醋、炆狗肉的姜并不甚辣,什么原因?久煎则辛辣味挥发之矣。所以越是大剂,必用水越多,用水越多必然久煎。所以大剂与温热,并不成正比,小剂量可能温热更甚。
(李保柱《仲景方术》:古代经方属于禁方的范畴,因属于秘方,所以故意在一张处方中,既使用标准度量衡,又使用非标准度量衡,其目的就是不让外人搞清楚准确剂量和搭配,开方之人明知半夏用半斤八两,但故意用半升以表示,让你搞不清究竟是多重的量。桂枝汤全方十六两以对应太阳归藏数16,知道全方的归藏数是十六,用已知数求未知数法则,就可知道大枣是五两,因为保守和保密思想的存在,故用12枚不确定的剂量以示人,而枣有大小之分,不同的产地和品种其十二枚枣的重量是不同的,山西河东晋南产的红枣才称其为大枣,选取十二枚用秤秤之,正好是五两之数,合今之50克,那么不用五两大枣,用二两或三两大枣,虽然也有治疗效果,但仍然不是最佳量效关系,其疗效肯定有差异。整理者:李保柱之意,仲景一两=现今10克。)
广州市已故“市名老中医”吴粤昌老师编著的《岭南医徵略》,其中载民国1932年间,广州惠福西路温良里八号,有一位叫谭孟勤的中医,“处方不出十许味变化,每方只四五味、六七味而止。惟细辛、川椒、胡椒、干姜、炮天雄、荜拨、薤白、半夏等,药量奇重,细辛恒三四两至七八两,川椒、胡椒三四两,干姜、炮天雄二三两,他药称量,统计一方重剂恒达四十余两,轻剂亦十余二十两。用清水一坛,久煎剩二三碗,去滓再煎至一碗,候冷饮之…奏效如抻…信服者众,求诊者愈多”。
此事我记起20世纪70年代初,粤剧老艺人丁公醒对我说,他年轻时患肺结核,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医生,开的药全是辛辣之品,用大牛头煲煎煮,后来便好了。我当时没在意。前年与著名粤剧演员罗家宝谈起,他说当年是粤剧名丑王中王把惠福路一姓谭的医生叫谭大剂的处方给丁公醒的,粤剧行内很多人都知,那医生的药又辣又酸、又臭又苦。因此想必是此谭孟勤了。
《岭南医徵略》又引用当时著名西医张公让先生《中西医学比观》说:“潭孟勤先生的处方,也不是毫无效验的。…观察谭先生之药,久煎药效消失殆尽,虽大剂犹小剂也”。
再联想近来热门非常的“火神派”用药剂量蛮大,是否也可如是观之?
六、寒热并用
经方寒热并用,又为仲景组方的一大法门。除针对病机寒热互见、寒热互用的,如半夏泻心汤、柴胡桂枝干姜汤、乌梅丸等方。也有因阴盛格阳虽反佐而用的,如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但为监制温药,佐以寒药,令能耐药者,实际应用中,占不少比例。所谓“去性取用”。如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外证是喘而兼有烦躁,小青龙汤为热药(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往往服后有烦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之象,《伤寒论》第41条),稍有渴,或痰黄白相间,或舌苔黄都可加石膏。即使未见烦躁也可加石膏。
又如桂枝芍药知母汤,为治历节:“诸肢节疼痛,身体尫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此方一派温药,配上芍药、知母之寒。而方证描述上未见有热象,故组方原意可能就是借寒润以制温燥。其实经方中多有此意,不必强解。
又如续命汤之石膏,可能是该汤中最受争议的一味药。为何在大队辛温之品中,配以甘寒之石膏呢?续命汤目的在于温散血脉凝滞,佐以石膏等寒凉之品,并非为了如后世所说的清肝经上亢之火,或清肺经阴伤之热,仲景使用石膏主要是为了防止药物过于温热。晋唐时各“凉续命”中有黄芩、葛根、荆沥等也是此意。再有温经汤之麦冬等,都含此意,不一一列出。
七、大枣、甘草调和药性
详见《从桂枝汤说起,谈谈经方的药物配对》。
八、杂疗诸方
仲景书中,一般已冠名之方,多取自《汤液经》等,也有出自某人之方如越婢汤、候氏黑散、续命汤等,但都已经仲景结合自己经验,整理定型,故风格融为一体,不着痕迹。如续命汤,是宋臣校正《金匮要略》时,从《古今录验》补入。从方名看似非仲景惯用,是仲景书正文中唯一一首以夸耀疗效命名的方。但从风格上确为仲景方。故《千金翼》说:“此仲景方,神秘不传”。观《千金》、《外台》诸书以“续命”为名之方有数十首,药虽有出入,但主药相同,看来当时已是颇为流行的一首方。
《金匮要略》杂疗第二十三、禽兽虫鱼禁忌第二十四及果实菜谷禁忌等二十五3篇中,载有多方,但此类方,一来多未命名,药味少,方法简便。二来多用治仓促急证。如“还魂汤”(麻黄、杏仁、甘草。《千金》有桂心。即“麻黄汤”矣)。这类方,大多取材于民间,或未必经仲景用过,故未命名,风格会各异。
观仲景书各冠名方剂,组方用药,风格突显,全书前后连贯,有规有律。总的来说,探索经方辨证、组方、用药规律是学习《伤寒杂病论》的必由之路,也是捷径。
(注:此原为黄师2010年7月12日与其旅澳师兄卢正平切磋对话,后成文)
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参考《汤液经法》为主,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编写成《伤寒杂病论》。其处方风格自成一派,为后世之垂范。
一、组方原则以临床为据,不依《内经》更非《易经》
自宋以后,多以《内经•至真要大论》所说为组方原则。特别近现代的教科书,更认定仲景制方是谨遵《内经》之训的。《内经•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其实无讲“佐”)。因此,解释麻黄汤为例:君--麻黄(发汗解表),臣--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佐--杏仁《助麻黄平喘),使--甘草(协和诸药)。如此解释或者可以解释麻黄汤主药次药是什么。但是否完全代表了仲景制方的原意,恐怕还是可以斟酌的。细读《伤寒论》原文便知仲景用桂枝实有监制麻黄之意,那就不是作为臣药可以解释得通的了。
《内经•至真要大论》又说:“汗者不以为奇,下者不以为偶”。但仲景峻汗之剂的“大青龙汤”却是七味药;峻下之剂“大承气汤”却是四味药。那么仲景岂非不循圣人之教,离经叛道?《内经•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在唐•王冰前是不见流传的,王冰“时于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才刊行于世。可见仲景立方之时未识本此,更遑论《汤液经》了。
至于方剂学的组成法则,把“使”药的作用强调,而有了“引经药”之说。“使”药的作用能引导君药直达病所,乃金元时期才出现的。葛根入阳明、柴胡归肝经…以及升麻升提,桔梗为舟楫之剂,诸花皆升、金石下沉等升降之说。至有把经方中难以理解的似乎便可迎刃而解了。如续命汤乃千古奇方,何以方中干姜、石膏同用?也把它诠释为痱病乃脾胃的升降失司,因而用干姜之辛温刚燥、升脾气,石膏质重而具沉降之能,所以脾胃升降功能得复,是治痱之本也。那么,“使”药便似乎成为无可替代的主药矣。难道也是仲景的原意吗?
《内经》运气七大篇,是唐代以后才介入中医学中,真正运用恐怕要更后,姑勿论运气学说的价值有多大。汉时仲景有否遵循运气、易学去制订方剂?易学医家必说是肯定的。兹录两段方解共赏。
1.五苓散。李阳波讲述、刘力红等整理的《开启中医之门•第四讲•规矩之道》中说到:“为什么它叫五苓散呢?首先运用了声韵训诂的方法,将苓训为令。令就是节令,加上一个草头,是说明植物生长与节令密切相关,一年之中,春夏秋冬长夏,也刚好是五令,这个五令又跟东南西北中,寒热温凉湿相关,因此,五苓散应该是与此相关的一个方剂。先看白术、桂枝、茯苓三味药,白术性温、桂枝性热、茯苓性平,温者东方春令之气,热者南方夏令之气,平者中央长夏之气,这里已经解决了三令,或曰三苓;还有猪苓、泽泻,按照五令五方五行的配属,北方冬令水属,水属若与动物相配,则正好与猪属相配,因此,猪苓在这里显然应该属北方冬令之气。剩下一个泽泻当然是配西方,坎离異震艮兑乾坤而配水火风雷山泽天地…其中兑泽位西,刚好与泽海相对应…五苓散的主要作用是通利水湿,而且它是分利东南西北中之湿(沛按:仲景哪条条文说五苓散治东南西北中之湿?)。当北方肾的气立出了问题而出现湿时,就应该用南方的桂枝(沛按:桂枝不是辛温吗?要辛热改附子都一样?)去对治,南方心…应用北方的猪苓(沛按:猪苓与猪有直接关系?如此说,仲景不如广东人用猪小肚(猪膀胱)煲车前草以利尿来得直接),去对治。西方…用东方白术(沛按:白术色白不是属西吗?)去对治,东方…用西方泽泻(沛按:泽漆也是泽,可以吗?)去对治,中央则用茯苓…为什么张仲景的东西这么严谨(沛按:这就叫严谨)?它已经就像我们在演算数学題目、物理题目一样”。上述一段话,也是不论正确与否,我只想问,当日仲景真是把五令故意写成五苓的吗?仲景其他方都是这样推算制订出来的吗?当然,刘教授会说仲景是这样的,如果仲景不会《易经》就当不成医圣了。
2.炙甘草汤。刘力红博士在《思考中医》317页中这样代表仲景解释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指两方的大枣数)颠倒过来?…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
好了,我不厌其烦,大篇幅引用这些论说。让大家试试,把炙甘草汤的大枣抽出五枚看这个方的功效会否质变,把当归四逆汤大枣多用五枚能否把它变成养阴方?我无心找仲景其他方反证其谬,但我坚信仲景不是根据《内经》的原则,更不是根据《易》的象数去制方的。众所周知,仲景是一个实践家、临床家(集论家,收集整理是也),因此,连处方用名都要“避道家之称”(刘教授可以说:正因为要避道家之称故把五令改五苓)。仲景制方是以临床为依据,“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我们看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35~40条。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青龙汤已下,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苓桂味甘汤”。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苓甘五味干辛汤,以治其咳满”。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苓甘五味姜辛夏汤”。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若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上述从小青龙汤加减衍变至苓甘五味姜辛夏仁大黄汤。可见仲景立方遣药有证有据,为什么小青龙汤要精简成苓桂味甘汤?为什么要去桂枝,又复加姜辛?为什么本来要用麻黄但勉用杏仁?为什么加半夏,为什么加大黄?思路讲得清清楚楚,何劳五行八卦推算一番。“读仲景书,于无字处求之”,谬也!
二、参考《汤液经法》处处紧贴临床,超越《汤液经法》
《甲乙经•序》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林亿在宋本《伤寒论》序中说:“伊尹本神农之经,仲景本汤液之法”。但是《汤液经》已不可见,其原貌怎样,无人知晓。1967年河北老中医张大昌向北京中医研究院献出古本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手抄本。自此,世人得见《汤液经》的概貌。
我们关心的是,《辅行诀》是一本什么书,以及与《伤寒论》的关系。此书卷首题曰:“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是书从《汤液经法》诸方中“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又曰:“汉晋已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佗、吴普、皇甫玄宴、支法师(引自《辅行诀》疑为支法存,晋以前名医)、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又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治疗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又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从此书可见:
1.《汤液经》一名,最早见录在《汉书•艺文志》经方类中。观陶氏所提及汉晋名医多人“咸师式此”,可见汉晋时《汤液经》尚颇流行。与《甲乙经》所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及宋•林亿所说吻合。20世纪40年代末,杨绍伊因“论广”二字疑及《伤寒论》是据《汤液经》扩充。因当时未见实物,故未引起人重视。今确信仲景乃“论广”之耳。
2.陶氏乃道家,《辅行诀》者,是辅助道士修行、“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的真“诀”(道家常用“诀”字)。但只检用常情六十首(现见仅四十六首,恐已是经后人删减),陶氏说::“《汤液经》…方亦三百六十首”。而仲景论广,只检选部分,自己增添部分。
3.“仲景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事实上,《伤寒论》之方多以某药名之,可见仲景不尚玄理、不尚浮夸,甚至形容疗效的方名都很少,不若后世什么“神效”、“仙方”等。当然现在看到的《伤寒论》尚有阳旦、青龙、白虎之名。姜春华1985年曾撰文提及“论中白虎、青龙之名犹存者,想为魏晋人依《汤液》而改”。
4.仲景根据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撰为《伤寒论》。例如所谓二旦,即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桂枝汤,大阳旦汤即《金匮要略》黄芪建中汤,小阴旦汤即《伤寒论》黄芩汤加生姜,大阴旦汤即《伤寒论》小柴胡汤。例如《辅行诀》所载“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咽中干,每喜干呕,食不下,心中烦懑,胸胁支痛,往来寒热者方”。而到了《伤寒论》仲景则把“口苦,咽干,目眩”另立为“少阳之为病”一条,可见仲景“论”之,有了太阳、阳明、少阳之病,不再是纯方书。而小柴胡汤在《伤寒论》中有20条条文之多。可见仲景根据自己的临床所见和体会,加以“广”之。把小柴胡汤的适应证、宜忌、如何灵活运用、加减法说明,并把此方衍化成多方。淋漓尽致,理法方药皆全。又如《辅行诀》小白虎汤即《伤寒论》白虎汤,而仲景把《辅行诀》小白虎汤条文:“治天行热病,大汗出不止,口干舌燥,饮水数升不已,脉洪大者方”。改成为白虎加人参汤证,方在白虎汤中加人参。而另立白虎汤方证。如此更切合临床,层次分明。尤其是加人参,更是高明。
三、选药多自《神农本草经》,绝不芜杂
清•徐大椿曰:“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共用药物仅156味,其中《伤寒论》仅用93味,核心药物不外乎四五十味。仲景运用这些药物,巧妙组合,却足以对付临床常见病。而这93味中,载于《神农本草经》者有81味。汉时新药的发现当然不如后世之多。但是经汉前历代的经验总结,疗效肯定。再经组合,而成经典用方。
四、用药精专,甚少重叠
仲景的处方风格,不能不说其方,一证一药,甚少一证多药者,即甚少作用相同的药重叠使用。即使如“五苓散”也非如上所说“通利水湿”,如只以通利水湿,仲景是不会四味利水药齐用的。五苓散方证条文《伤寒论》、《金匮要略》共11条。归纳其证有:①“小便不利”。②“烦渴”或“汗出而渴”或“渴而口燥烦”或“微热消渴”。③“渴欲饮水,水入则吐”。④“脐下有悸”。⑤“吐涎沫而癫眩”。五类见证,其次还有“肉上粟起”等。归咎其病机为水湿内停,气化不利,津液不布。治固应利水化气。但选药却甚具针对性。简言之,五味药就是围绕上述五类症状而设的:
如“脐下有悸”--以苓桂(悸用桂或加苓,乃仲景通则)。
“癫眩”、“水入则吐”--以泽泻、白术(苦冒眩者泽泻汤主之,“冒者必呕”)。
“消渴”--以猪苓、泽泻(猪苓汤、肾气丸皆有渴,可证之)。
绝非什么春夏秋冬长夏对东南西北中,虚泛飘忽可比。亦非四苓叠用,通利水湿。尝见时人开的处方,说是用经方,每每下笔似流水,叠床架屋,动手便是十六七味。主次不明,原方影子难寻,面目全非。如某名家治咳喘,处以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姑勿论其辨证是否对应此方。仲景原方七味,尚加入紫苑、苏子、百部、前胡、黄芩、鱼腥草,共成十四味,均是清化热痰之品。可见处方之人,恐仲景方药力不逮,毫无信心,故而叠用。对自己辨证同样不自信任,心虚无定见,故而为之。
五、急、重用简
仲景方中,急重之证,药多精专。这是合情合理的:急、重之证,药少则用水少。煎煮时间不用太长,利于救治;急、重之证,药重而用宏,直达病所,解决主要矛盾。此类情况,仲景或以二三味为方,或以水二或四升,煎取一二升,采取急煎急服的办法。
第一,四逆汤类方,以回阳救逆为目的。如“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方用:附子一枚(生,破八片)、干姜一两半、甘草二两(炙)。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而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等,都是单捷小剂。即便如“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苦冒眩者,冒眩较重,不堪其苦也,用泽泻汤,以泽泻五两、白术二两。相对量重而味少,其煎法也是“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不若如炙甘草汤之“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取三升”用水、酒共十五升,则煎煮时间长矣。
第二,承气汤类急下之剂。如当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时用的大承气汤仅四味。治“胸痹”之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都是三味。治“心胸中大寒痛”之大建中汤仅三味。还有大黄附子汤等治急症之方,无不是单捷小剂。直趋病所,解决主要矛盾。
经方用量历来争议较大,由于古今度量衡差别较大,存在多种说法,近年来较权威的折算法,多依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1984年),汉一两折合今之13.92克。1995年上海柯雪帆以出土的汉代“大司农(汉代司掌度量衡的政府部门)颁的“权”进行考证,汉之一两合今之15.6克。当然,有人认为古有“神农秤”(药抨),汉之一两折合今之1~1.6克,但没有实物考证。梁•陶弘景、唐•孙思邈均未有应用。如按吴氏、柯氏的考证,对照现代一般临床医生用量,及《药典》所载用量,仲景书的用量都是相对较重的。我认为仲景书以临床为依归,所以药量较重是其风格。事实上按其用量也是较安全的。中医历来有“医者意也”、“四两拨千斤”之说法。毕竟用量太轻,是达不到治疗效果的。但近又有人把药量越用越重,附子等温热药每用750克,我认为却没有必要,观仲景温经止痛用附子量可稍大,一枚至三枚(如桂枝附子汤,三枚,炮),而温里回阳则均用一枚,通脉四逆仅大者一枚,但生用。看来是急煎,水少,急服的原因。清代广东东莞经方名医陈焕堂之《仲景归真》第一卷曰《伤寒醒俗》,意思即针砭时医之流弊,力倡仲景之正流,其中有一段提到:有人用三钱五钱生姜便谓量重,尝见广东人妇女产后,用数十斤老姜煲醋,并不觉热。我觉得他这个举例值得深思,颇具启发。①姜性虽温,但非如鸠鸩,看广东人炆鸭、炆狗肉、炆鲤鱼何不是放三五两生姜?何温之有?②凡烫姜醋、炆狗肉的姜并不甚辣,什么原因?久煎则辛辣味挥发之矣。所以越是大剂,必用水越多,用水越多必然久煎。所以大剂与温热,并不成正比,小剂量可能温热更甚。
(李保柱《仲景方术》:古代经方属于禁方的范畴,因属于秘方,所以故意在一张处方中,既使用标准度量衡,又使用非标准度量衡,其目的就是不让外人搞清楚准确剂量和搭配,开方之人明知半夏用半斤八两,但故意用半升以表示,让你搞不清究竟是多重的量。桂枝汤全方十六两以对应太阳归藏数16,知道全方的归藏数是十六,用已知数求未知数法则,就可知道大枣是五两,因为保守和保密思想的存在,故用12枚不确定的剂量以示人,而枣有大小之分,不同的产地和品种其十二枚枣的重量是不同的,山西河东晋南产的红枣才称其为大枣,选取十二枚用秤秤之,正好是五两之数,合今之50克,那么不用五两大枣,用二两或三两大枣,虽然也有治疗效果,但仍然不是最佳量效关系,其疗效肯定有差异。整理者:李保柱之意,仲景一两=现今10克。)
广州市已故“市名老中医”吴粤昌老师编著的《岭南医徵略》,其中载民国1932年间,广州惠福西路温良里八号,有一位叫谭孟勤的中医,“处方不出十许味变化,每方只四五味、六七味而止。惟细辛、川椒、胡椒、干姜、炮天雄、荜拨、薤白、半夏等,药量奇重,细辛恒三四两至七八两,川椒、胡椒三四两,干姜、炮天雄二三两,他药称量,统计一方重剂恒达四十余两,轻剂亦十余二十两。用清水一坛,久煎剩二三碗,去滓再煎至一碗,候冷饮之…奏效如抻…信服者众,求诊者愈多”。
此事我记起20世纪70年代初,粤剧老艺人丁公醒对我说,他年轻时患肺结核,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医生,开的药全是辛辣之品,用大牛头煲煎煮,后来便好了。我当时没在意。前年与著名粤剧演员罗家宝谈起,他说当年是粤剧名丑王中王把惠福路一姓谭的医生叫谭大剂的处方给丁公醒的,粤剧行内很多人都知,那医生的药又辣又酸、又臭又苦。因此想必是此谭孟勤了。
《岭南医徵略》又引用当时著名西医张公让先生《中西医学比观》说:“潭孟勤先生的处方,也不是毫无效验的。…观察谭先生之药,久煎药效消失殆尽,虽大剂犹小剂也”。
再联想近来热门非常的“火神派”用药剂量蛮大,是否也可如是观之?
六、寒热并用
经方寒热并用,又为仲景组方的一大法门。除针对病机寒热互见、寒热互用的,如半夏泻心汤、柴胡桂枝干姜汤、乌梅丸等方。也有因阴盛格阳虽反佐而用的,如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但为监制温药,佐以寒药,令能耐药者,实际应用中,占不少比例。所谓“去性取用”。如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外证是喘而兼有烦躁,小青龙汤为热药(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往往服后有烦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之象,《伤寒论》第41条),稍有渴,或痰黄白相间,或舌苔黄都可加石膏。即使未见烦躁也可加石膏。
又如桂枝芍药知母汤,为治历节:“诸肢节疼痛,身体尫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此方一派温药,配上芍药、知母之寒。而方证描述上未见有热象,故组方原意可能就是借寒润以制温燥。其实经方中多有此意,不必强解。
又如续命汤之石膏,可能是该汤中最受争议的一味药。为何在大队辛温之品中,配以甘寒之石膏呢?续命汤目的在于温散血脉凝滞,佐以石膏等寒凉之品,并非为了如后世所说的清肝经上亢之火,或清肺经阴伤之热,仲景使用石膏主要是为了防止药物过于温热。晋唐时各“凉续命”中有黄芩、葛根、荆沥等也是此意。再有温经汤之麦冬等,都含此意,不一一列出。
七、大枣、甘草调和药性
详见《从桂枝汤说起,谈谈经方的药物配对》。
八、杂疗诸方
仲景书中,一般已冠名之方,多取自《汤液经》等,也有出自某人之方如越婢汤、候氏黑散、续命汤等,但都已经仲景结合自己经验,整理定型,故风格融为一体,不着痕迹。如续命汤,是宋臣校正《金匮要略》时,从《古今录验》补入。从方名看似非仲景惯用,是仲景书正文中唯一一首以夸耀疗效命名的方。但从风格上确为仲景方。故《千金翼》说:“此仲景方,神秘不传”。观《千金》、《外台》诸书以“续命”为名之方有数十首,药虽有出入,但主药相同,看来当时已是颇为流行的一首方。
《金匮要略》杂疗第二十三、禽兽虫鱼禁忌第二十四及果实菜谷禁忌等二十五3篇中,载有多方,但此类方,一来多未命名,药味少,方法简便。二来多用治仓促急证。如“还魂汤”(麻黄、杏仁、甘草。《千金》有桂心。即“麻黄汤”矣)。这类方,大多取材于民间,或未必经仲景用过,故未命名,风格会各异。
观仲景书各冠名方剂,组方用药,风格突显,全书前后连贯,有规有律。总的来说,探索经方辨证、组方、用药规律是学习《伤寒杂病论》的必由之路,也是捷径。
(注:此原为黄师2010年7月12日与其旅澳师兄卢正平切磋对话,后成文)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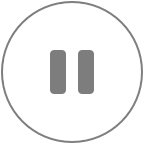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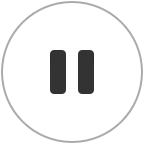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