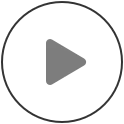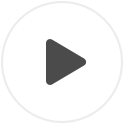透过诸位临床大家的不同视点:柴胡桂枝干姜汤小议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何莉娜
柴胡桂枝干姜汤见于《伤寒论》第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另《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篇》附方:“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组成:柴胡半斤,黄芩三两,桂枝三两,干姜二两,瓜蒌根四两,牡蛎二两,炙甘草二两。共七味,实乃小柴胡汤之变方也。即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法夏,加干姜、桂枝、牡蛎、瓜蒌根。
历代医家对柴胡桂枝干姜法的分析
少阳病兼水饮内结。伤寒汗下后,邪入少阳,枢机不利,疏泄失常,决渎失职,而致水饮内结。《伤寒论译释》、日本吉益东洞的《类聚方》及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皆持此意见。唐容川于《伤寒论浅注补正•太阳篇》说:“水饮内动,逆于胸胁,故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水结则津不升,故渴,此为猪苓汤证同一意也”。陈慎吾将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概括为“少阳证而有阴证转机之人用之”,即认为本方主治小柴胡汤证而有脾阳虚及心阳虚,阴虚不能化气而致水湿内停者。
2.邪陷少阳,胆火内郁兼太阴虚寒。刘渡舟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是仲景为邪陷少阳、胆火内郁兼太阴虚寒之证而设的。他在《伤寒论通俗讲话》中指出:“邪陷少阳,气郁不舒,故胸胁满微结;胆火上炎而灼津,故心烦口渴;热郁不得宣泄而上蒸,故头汗出;正邪纷争,故往来寒热;无关乎胃,故不呕;三焦气机阻滞,所以小便不利;内伤脾气,太阴虚寒,故见腹满或大便溏泻,此证为胆热脾寒,故治以清少阳之热,兼温太阴之寒”。在《伤寒论十四讲》中又说:“余在临床上用本方治疗慢性肝炎,证见胁痛、腹胀、便溏、泄泻、口干者,往往有效。若糖尿病见有少阳病证者,本方也极合拍”。
3.寒热错杂,上热下寒。胡希恕认为:“伤寒五六日,虽已发汗。并不解则常转入少阳柴胡证,医者不详查,而又误用下法,津伤甚,由阳证转化为阴证,虽胸胁满未去,但呈现微结。汗、下、邪热皆伤津液,津液不下,故小便不利;津液虚少,热伤津致燥,故渴而不呕;气冲于上,故但头汗出;往来寒热,为邪还在半表半里;心烦,为上有热”。这里的“微结”,是针对大陷胸汤证说的,即是说此结轻微,与大陷胸汤证结如石硬为阳明证者显异。
4.少阳病兼津伤。汗后复下,津液已损,更因邪入少困,胆火内郁,热耗津液,致亡津而内燥。如汪苓友云:“小便不利者,因下后下焦津液不足也”。
5.少阳病兼表邪未解。伤寒治疗不当,邪气内陷,表邪未解。如成无己谓:“即邪在半表半里为未解也”。尤在泾在其《伤寒贯珠集》中指出:“夫邪聚于上,热胜于内,而表邪不解”。
6.汗下阳陷,阴阳两伤。汗下后津液耗伤,又因苦寒妄下,阳气亦损,冉雪峰认为:“外则少阳而兼太阳,内则阳微而兼阴微,既为太阳少阳的里层,又为阳伤阴伤的并合”。
黄师对柴胡桂枝干姜汤方证的理解
此方结构奇特,寒热互用,加上原文语焉不详,致令注家众说纷纭,颇具争议。但如何用之临床,才是关键。黄师综合各家之说,紧密联系临床,对本方应用颇具心得。
从方证、病机而言,注家多以为乃少阳病而兼饮邪内结。然仲景治饮多以苓、术剂而本方何以不用?故黄师赞同刘渡舟之说,乃少阳胆热更兼太阴脾寒。而据刘老说,他是取自于陈慎吾前辈的启发:“少阳病而又兼见阴证机转”。刘老认为原文虽无下利记载,此证下利、腹胀却是临证特点。此一特点,指出了临床使用指征。此推论实又来于仲景,论中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以药测证,下利用干姜亦仲景之定例也。
“胸胁满微结”一证,胡希恕则从《皇汉医学》之说,“结”即含悸、气上冲之意。黄师认为日人此方医案,多有悸、气上冲。是从临床中来,也是仲景用桂枝之定例,可备临床参考。但“结”却未必是悸,仍应从结硬去理解。微结即微硬,胸胁胀满且有微硬。故本方用桂枝、牡蛎,是散结软坚之用。从病机来说,则不止是胆热脾寒矣,应有血结瘀阻矣。瓜蒌根一药,本证有渴,自然用之,仲景用瓜蒌根共十处,文中明言渴者七证。而用本品与附子、桂枝、干姜、细辛,也有与黄芩、瞿麦等同用。而白虎加人参汤之大烦渴不解反而不用花粉,五苓散证之消渴也不用花粉,肾气丸之消渴,以饮一斗,小便一斗都不用花粉。何也?是仲景对于这等严重的渴,必须从根本去解决问题。而知本方之用花粉是非阴津亏竭者。
黄师认为本方证除胆热脾寒兼血结在里之外,更应结合《金匮要略》原文理解:①本方见于疟病篇,疟疾有疟母,胸胁满微结可以理解。②原文曰:“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此寒、热不但指症状,亦指病机而言。所以本方证应是寒多而热少,脾寒重于胆热也。
临床应用此方,亦数刘、胡二老最有心得。他们多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红斑性狼疮等。黄师有个感觉,凡有干姜之方,可用于免疫系统的疾病;曾令我们做过干姜临床文献综述。我们发现黄师的假想有一定道理。本文介绍之张某案,为肝脓肿术后肝功能迟迟未复。证有大便微溏,但又有舌苔黄者。故加胆草、熟大黄以加重泄胆之热,效果理想。
典型病例
刘渡舟教授验案两则
例1:史某,女,60岁,退休干部,北京人,于1986年7月20日初诊。3年前确诊冠心病。近2个月来心情不快而出现心动悸、脉结代。心电图提示:频发室性早搏。经中西药(西药乙氨碘呋酮类;中药如炙甘草汤等)治疗,效果不明显。刻下心悸而烦,口苦且干,口渴,两胁疼痛连及后背,手指麻木,大便溏稀,日行3~4次,不思饮食,午后腹胀,小便不利,舌边尖红,苔白水滑,脉弦缓而有结。参合脉证,证属太阴脾家虚寒,少阳肝胆郁热而致胸阳不振,血脉不利。拟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12克,黄芩6克,干姜10克,桂枝10克,花粉10克,牡蛎30克,炙甘草12克,茯苓30克。4剂,水煎服。
7月24日复诊,大便稠,日行一次,腹胀消,心悸明显减轻,脾胃之气渐复,继上方7剂。
8月1日三诊,药尽诸症皆愈,心电图复查:大致正常。更方苓桂术甘汤加太子参15克,数剂巩固其效。追访至今未复发[1]。
例2:刘某,男,48岁,干部,北京市人。于1986年5月3日初诊。患者自述患糖尿病3年余,血糖380mg,尿糖(++++)。有肝炎和胆囊炎病史。先后服用降糖灵等多种药物。近半年来因心情不畅、劳累过度,诸症加重,经人介绍前来诊治。刻诊:口渴咽燥,渴欲饮水,口苦,胸胁满而心烦,便清,日行2-3次,不思饮食,食后腹胀,舌红苔薄白,脉弦而缓。血糖380mg,尿糖(++++)。证属胆热脾虚之证。治用柴胡14克,黄芩10克,干姜10克,桂枝10克,花粉15克,牡蛎30克,炙甘草10克。7剂,水煎服用。
药后5月10日复诊,口渴大减,口苦消失,继用前方7剂后,诸症均减,唯自感乏力,上方加太子参15克,服12剂,诸症愈。复查:血糖120mg,尿糖(-),随访2年未复发[2]。
黄师验案三则
例1:张某,素体健,2009年2月16日开始出现持续发热,最高39.5℃,咳嗽,痰黄,无恶寒、汗出,当地医院诊为肺炎,抗生素治疗近1个月。发热症状时好时坏,但觉全身乏力,胸胁闷满,伴有隐痛。2009年2月21日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行B超、CT及穿刺,诊断为肝脓肿。抗感染及护肝治疗,3月17日发热已退,肝功能改善出院。出院时B超:肝区仍有小结块,考虑肝脓肿未完全吸收。出院后仍觉肝区胀满,善太息,时有隐痛,饮食无味,尤忌荤腥,夜难安寝,易烦躁,面色苍黄无泽,大便稀溏不爽,易口渴。故来求诊。黄师即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柴胡24克,黄芩15克,干姜6克,花粉30克,牡蛎30克,桂枝15克,炙甘草15克,大黄15克,白芍60克,胆草6克。
4月27日复查肝功能:ALT:53mmol/L,AST:80mmol/L,TP:76.9mmol/L,GLB:27.6mmol/L。坚持服药3个月,转氨酶基本正常。ALT:33mmol/L,AST:26mmol/L,,已无肝区闷痛,饮食有味,睡而安寝,精神畅旺。现仍坚持服药巩固。
例2:黄师又曾治一香港患者,乳腺癌转移肺、胸骨、肝。腹水,胁痛,脘胀,胸胁满,下肢浮肿,口干渴不欲饮,便溏,舌红鲜艳如“红包”,无苔,舌边尖溃疡。先以甘草泻心汤加安桂芯、花旗参、附子,1周后舌烂舌红改善。再以本方复加党参、重用白芍。再2周下肢浮肿消退,精神好,症情稳定,取得近期疗效。
例3:又治东莞李某,肝癌介入术后,精神不振,面色暗滞,胸满腹胀,纳差,口干,便溏,舌苔黄腻。用此方后精神转佳,各项检验指标稳定。
参考文献
1.冯建春.刘渡舟教授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经验举隅[J].山西中医,1989,5(8)1-2
2.原文缺。
柴胡桂枝干姜汤见于《伤寒论》第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另《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篇》附方:“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组成:柴胡半斤,黄芩三两,桂枝三两,干姜二两,瓜蒌根四两,牡蛎二两,炙甘草二两。共七味,实乃小柴胡汤之变方也。即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法夏,加干姜、桂枝、牡蛎、瓜蒌根。
历代医家对柴胡桂枝干姜法的分析
少阳病兼水饮内结。伤寒汗下后,邪入少阳,枢机不利,疏泄失常,决渎失职,而致水饮内结。《伤寒论译释》、日本吉益东洞的《类聚方》及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皆持此意见。唐容川于《伤寒论浅注补正•太阳篇》说:“水饮内动,逆于胸胁,故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水结则津不升,故渴,此为猪苓汤证同一意也”。陈慎吾将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概括为“少阳证而有阴证转机之人用之”,即认为本方主治小柴胡汤证而有脾阳虚及心阳虚,阴虚不能化气而致水湿内停者。
2.邪陷少阳,胆火内郁兼太阴虚寒。刘渡舟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是仲景为邪陷少阳、胆火内郁兼太阴虚寒之证而设的。他在《伤寒论通俗讲话》中指出:“邪陷少阳,气郁不舒,故胸胁满微结;胆火上炎而灼津,故心烦口渴;热郁不得宣泄而上蒸,故头汗出;正邪纷争,故往来寒热;无关乎胃,故不呕;三焦气机阻滞,所以小便不利;内伤脾气,太阴虚寒,故见腹满或大便溏泻,此证为胆热脾寒,故治以清少阳之热,兼温太阴之寒”。在《伤寒论十四讲》中又说:“余在临床上用本方治疗慢性肝炎,证见胁痛、腹胀、便溏、泄泻、口干者,往往有效。若糖尿病见有少阳病证者,本方也极合拍”。
3.寒热错杂,上热下寒。胡希恕认为:“伤寒五六日,虽已发汗。并不解则常转入少阳柴胡证,医者不详查,而又误用下法,津伤甚,由阳证转化为阴证,虽胸胁满未去,但呈现微结。汗、下、邪热皆伤津液,津液不下,故小便不利;津液虚少,热伤津致燥,故渴而不呕;气冲于上,故但头汗出;往来寒热,为邪还在半表半里;心烦,为上有热”。这里的“微结”,是针对大陷胸汤证说的,即是说此结轻微,与大陷胸汤证结如石硬为阳明证者显异。
4.少阳病兼津伤。汗后复下,津液已损,更因邪入少困,胆火内郁,热耗津液,致亡津而内燥。如汪苓友云:“小便不利者,因下后下焦津液不足也”。
5.少阳病兼表邪未解。伤寒治疗不当,邪气内陷,表邪未解。如成无己谓:“即邪在半表半里为未解也”。尤在泾在其《伤寒贯珠集》中指出:“夫邪聚于上,热胜于内,而表邪不解”。
6.汗下阳陷,阴阳两伤。汗下后津液耗伤,又因苦寒妄下,阳气亦损,冉雪峰认为:“外则少阳而兼太阳,内则阳微而兼阴微,既为太阳少阳的里层,又为阳伤阴伤的并合”。
黄师对柴胡桂枝干姜汤方证的理解
此方结构奇特,寒热互用,加上原文语焉不详,致令注家众说纷纭,颇具争议。但如何用之临床,才是关键。黄师综合各家之说,紧密联系临床,对本方应用颇具心得。
从方证、病机而言,注家多以为乃少阳病而兼饮邪内结。然仲景治饮多以苓、术剂而本方何以不用?故黄师赞同刘渡舟之说,乃少阳胆热更兼太阴脾寒。而据刘老说,他是取自于陈慎吾前辈的启发:“少阳病而又兼见阴证机转”。刘老认为原文虽无下利记载,此证下利、腹胀却是临证特点。此一特点,指出了临床使用指征。此推论实又来于仲景,论中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以药测证,下利用干姜亦仲景之定例也。
“胸胁满微结”一证,胡希恕则从《皇汉医学》之说,“结”即含悸、气上冲之意。黄师认为日人此方医案,多有悸、气上冲。是从临床中来,也是仲景用桂枝之定例,可备临床参考。但“结”却未必是悸,仍应从结硬去理解。微结即微硬,胸胁胀满且有微硬。故本方用桂枝、牡蛎,是散结软坚之用。从病机来说,则不止是胆热脾寒矣,应有血结瘀阻矣。瓜蒌根一药,本证有渴,自然用之,仲景用瓜蒌根共十处,文中明言渴者七证。而用本品与附子、桂枝、干姜、细辛,也有与黄芩、瞿麦等同用。而白虎加人参汤之大烦渴不解反而不用花粉,五苓散证之消渴也不用花粉,肾气丸之消渴,以饮一斗,小便一斗都不用花粉。何也?是仲景对于这等严重的渴,必须从根本去解决问题。而知本方之用花粉是非阴津亏竭者。
黄师认为本方证除胆热脾寒兼血结在里之外,更应结合《金匮要略》原文理解:①本方见于疟病篇,疟疾有疟母,胸胁满微结可以理解。②原文曰:“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此寒、热不但指症状,亦指病机而言。所以本方证应是寒多而热少,脾寒重于胆热也。
临床应用此方,亦数刘、胡二老最有心得。他们多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红斑性狼疮等。黄师有个感觉,凡有干姜之方,可用于免疫系统的疾病;曾令我们做过干姜临床文献综述。我们发现黄师的假想有一定道理。本文介绍之张某案,为肝脓肿术后肝功能迟迟未复。证有大便微溏,但又有舌苔黄者。故加胆草、熟大黄以加重泄胆之热,效果理想。
典型病例
刘渡舟教授验案两则
例1:史某,女,60岁,退休干部,北京人,于1986年7月20日初诊。3年前确诊冠心病。近2个月来心情不快而出现心动悸、脉结代。心电图提示:频发室性早搏。经中西药(西药乙氨碘呋酮类;中药如炙甘草汤等)治疗,效果不明显。刻下心悸而烦,口苦且干,口渴,两胁疼痛连及后背,手指麻木,大便溏稀,日行3~4次,不思饮食,午后腹胀,小便不利,舌边尖红,苔白水滑,脉弦缓而有结。参合脉证,证属太阴脾家虚寒,少阳肝胆郁热而致胸阳不振,血脉不利。拟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12克,黄芩6克,干姜10克,桂枝10克,花粉10克,牡蛎30克,炙甘草12克,茯苓30克。4剂,水煎服。
7月24日复诊,大便稠,日行一次,腹胀消,心悸明显减轻,脾胃之气渐复,继上方7剂。
8月1日三诊,药尽诸症皆愈,心电图复查:大致正常。更方苓桂术甘汤加太子参15克,数剂巩固其效。追访至今未复发[1]。
例2:刘某,男,48岁,干部,北京市人。于1986年5月3日初诊。患者自述患糖尿病3年余,血糖380mg,尿糖(++++)。有肝炎和胆囊炎病史。先后服用降糖灵等多种药物。近半年来因心情不畅、劳累过度,诸症加重,经人介绍前来诊治。刻诊:口渴咽燥,渴欲饮水,口苦,胸胁满而心烦,便清,日行2-3次,不思饮食,食后腹胀,舌红苔薄白,脉弦而缓。血糖380mg,尿糖(++++)。证属胆热脾虚之证。治用柴胡14克,黄芩10克,干姜10克,桂枝10克,花粉15克,牡蛎30克,炙甘草10克。7剂,水煎服用。
药后5月10日复诊,口渴大减,口苦消失,继用前方7剂后,诸症均减,唯自感乏力,上方加太子参15克,服12剂,诸症愈。复查:血糖120mg,尿糖(-),随访2年未复发[2]。
黄师验案三则
例1:张某,素体健,2009年2月16日开始出现持续发热,最高39.5℃,咳嗽,痰黄,无恶寒、汗出,当地医院诊为肺炎,抗生素治疗近1个月。发热症状时好时坏,但觉全身乏力,胸胁闷满,伴有隐痛。2009年2月21日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行B超、CT及穿刺,诊断为肝脓肿。抗感染及护肝治疗,3月17日发热已退,肝功能改善出院。出院时B超:肝区仍有小结块,考虑肝脓肿未完全吸收。出院后仍觉肝区胀满,善太息,时有隐痛,饮食无味,尤忌荤腥,夜难安寝,易烦躁,面色苍黄无泽,大便稀溏不爽,易口渴。故来求诊。黄师即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柴胡24克,黄芩15克,干姜6克,花粉30克,牡蛎30克,桂枝15克,炙甘草15克,大黄15克,白芍60克,胆草6克。
4月27日复查肝功能:ALT:53mmol/L,AST:80mmol/L,TP:76.9mmol/L,GLB:27.6mmol/L。坚持服药3个月,转氨酶基本正常。ALT:33mmol/L,AST:26mmol/L,,已无肝区闷痛,饮食有味,睡而安寝,精神畅旺。现仍坚持服药巩固。
例2:黄师又曾治一香港患者,乳腺癌转移肺、胸骨、肝。腹水,胁痛,脘胀,胸胁满,下肢浮肿,口干渴不欲饮,便溏,舌红鲜艳如“红包”,无苔,舌边尖溃疡。先以甘草泻心汤加安桂芯、花旗参、附子,1周后舌烂舌红改善。再以本方复加党参、重用白芍。再2周下肢浮肿消退,精神好,症情稳定,取得近期疗效。
例3:又治东莞李某,肝癌介入术后,精神不振,面色暗滞,胸满腹胀,纳差,口干,便溏,舌苔黄腻。用此方后精神转佳,各项检验指标稳定。
参考文献
1.冯建春.刘渡舟教授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经验举隅[J].山西中医,1989,5(8)1-2
2.原文缺。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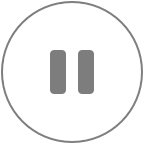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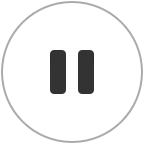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