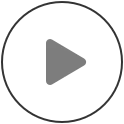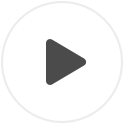随师体会:大美不言的仲景用药心法举隅
 加入书架
加入书架
潘林平
我的老师黄仕沛对经方有着真挚而执著的感情,他始终以孺子之心,锲而不舍地研究、实践经方,从不沽名钓誉、空谈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临床疗效显著,屡起沉疴。最难能可贵的是,黄师把宝贵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使我等后学之辈得益匪浅。得遇名师指点,是我从医路上最大的幸运和收获。黄师向来主张回归仲景原意,用仲景思想诠释经方内涵,在原著中探求经方的用药思路。仲景之方,方精、药少、效佳、果验,故黄师反对随意加减经方。跟从黄师学习,令我体会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兴兵须有理,用药要有因。“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历代兵家常胜者,必善用兵;历代医家有名者,必善用药。故以黄师传授的部分仲景用药心法,作为随师体会的内容,以求抛砖引玉,举一反三。
一、芍药
张仲景运用芍药独具特点,黄师从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到黄芪建中汤治虚劳里急,悟芍药诸方治诸挛急、腹痛。能体现此思路的经方有:芍药甘草汤、桂枝汤、桂枝加芍药汤、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黄芩汤、四逆散、大柴胡汤、当归芍药散、小青龙汤、真武汤。
芍药一味,其“止痛”作用早有记载。如《神农本草经》称芍药可“止痛”,能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张仲景时代芍药无赤、白之分,黄师在临床上,取其缓急止痛功效时多用白芍,并且用量宜大,多在45克以上,甚至用到120克,方能获效。
仲景常用芍药配伍甘草治疗诸痉挛、痛证,芍药甘草汤即为代表方及基础方。世称群方之冠的桂枝汤就是以芍药甘草为基础方组合而成。黄师在临床上用芍药甘草汤治疗脚挛急、腰腿疼痛、下肢不能屈伸者,其脚即伸,效果立竿见影。临床所见,芍药甘草汤不仅可治疗肢体肌肉痉挛,还可治疗胃肠痉挛,如阵发性胃痛、腹痛、膈肌痉挛(如呃逆)、支气管痉挛(如哮喘)、子宫痉挛(如痛经、产后腹痛)、血管痉挛(血管痉挛性头痛)等,疗效显著。
桂枝加芍药汤,“本太阳,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方中芍药用量达六两,专为腹满痛而设。《伤寒论》中治“法当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中治“虚劳里急,诸不足”的黄芪建中汤,方中芍甘合用,缓急止痛,亦是此用。
黄芩汤是芍药甘草汤加黄芩、大枣,是治疗热利的名方,临床上,以此方治疗兼见腹痛的下利效果最佳。
《伤寒论》第318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四逆散中的芍药、甘草,正是治疗其腹中痛的要药。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治》:“妇人怀娠,腹中疞痛,当归芍药散主之”。本方中芍药用量最重,达1斤,黄老常以此方治疗妇人痛经、妊娠腹痛等疾病。
《伤寒论》第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痛,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黄师认为,小青龙汤中白芍的作用是缓解支气管痉挛,从而缓解咳、喘等症状克。
此外,真武汤中白芍的作用向来备有争议。以原文及仲景用药思路观之,在真武汤证中有“腹痛”与“肌肉瞤动”,故以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真武汤之芍药为“腹痛”与“肌肉瞤动”而设,非为利水而设。
需要指出的是,芍药治疗的疼痛,多是功能性疼痛,以阵发性、痉挛性疼痛效果最佳,对器质性疼痛疗效多不佳。此外,芍药用于缓急止痛时用量较大,根据仲景用药规律,胸闷、心悸者不宜。《伤寒论》第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后世多知炙甘草汤以桂枝汤为基础组成,黄师却认为乃桂枝去芍药汤组成,以芍药不利于胸满,悸者多满。而吴氏加减复脉汤以炙甘草汤去参、桂、大枣、姜,加入芍药。黄师认为大谬也。如此去桂枝却加芍药,断不能治“心中憺憺大动”的。
二、桂枝
桂枝在经方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仲景在《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使用桂枝的配方接近30%,桂枝汤更是群方之首。但临床上很多医生认为其“过于温热”而弃用。黄师深得仲景用桂之心法,临床运用得心应手。黄师从桂枝甘草汤证“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悟仲景悸证诸方必用桂。体现此规律的经方有:桂枝甘草汤、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炙甘草汤;苓桂术甘汤、苓桂味甘汤、苓桂甘枣汤、五苓散;桂枝甘草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伤寒论》第64条:“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本条是使用麻黄后汗出过多,导致动悸,以桂枝甘草汤治疗,可见桂枝可以定悸。在使用麻黄的经方中,大多配有桂枝甘草,以防止心悸的出现。如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等。本方为治心悸的基本方,含有此思路的经方还包括: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炙甘草汤;“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的桂枝去芍药汤等。桂枝不限于治疗心悸,还可治疗其他部位的悸动感,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桂枝不仅治疗心悸,还可治疗有“气上冲”感的疾病。临床所见,此种感觉也是心悸的另一表现形式,只是很多时候程度比心悸严重。体现此思路的经方包括:《伤寒论》第15条:“太阴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第121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枝二两也”(另见(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并治》)。第67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第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青龙汤已下,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主之”。
桂枝还可治疗因惊恐等因素引起的情志异常,而这些情志异常均可伴见惊悸。如《伤寒论》第118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乳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小品》云:虚弱浮热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故曰二加龙骨汤)。《伤寒论》第112条:“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第107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俑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临床所见,桂枝的平冲定悸作用不容置疑。黄师认为:后世但知枣仁、远志、柏子仁、龙眼肉,宁心安神治心悸,但弃桂枝治悸,甚为可惜。黄师治疗心悸时多用15克以上,治疗“气上冲”更大,可用至20克,甚至45克。张仲景时代并未细分桂枝与肉桂,随师所见,重症顽疾黄师多用肉桂,或者肉桂与桂枝同用,其余多用桂枝。随师所见治关老太婆奔豚,便是30克桂枝,与肉桂6克同用。
三、干姜
随师曾见黄师治一王姓妇人,支气管扩张病史多年,每晨必咯痰清稀盈碗,用甘草干姜汤合麦门冬汤治之收效甚显,可见干姜之用甚为微妙。干姜在经方中用得极为广泛,黄师运用干姜主要有二:一是虚寒性分泌物增多之证,如咳嗽泡沫痰、小便量多而清稀、腹泻水样便、呕吐痰涎等,“诸病水液,澄澈清冷”者皆可用之(“病痰饮者,当以药温之”是也)。二为治疗免疫相关性疾病,黄师根据临床经验提出干姜可能有调节免疫的功效。如以桂枝甘草干姜汤治疗肝硬化、甘草泻心汤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等。
黄师指出,经方遗尿之证有三:
一者《伤寒论》219条:白虎汤证之“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恻,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实为热闭神昏之遗尿。
二者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实则矢气,虚则遗尿,名曰气分”。
三者,便是甘草干姜汤了。此方可治疗遗尿,悟出肾着汤也可治遗尿,而治疗遗尿的主药是干姜(遗者,阳不敛阴也,膀胱括约肌失束也,机能低下也,温阳病自愈)。《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黄师曾以此方并控制饮食,治愈一孕妇糖尿、羊水过多,以其身重腰中冷、小便频为要点。
经方中治饮之方有:半夏干姜散(半、姜)、苓甘五味姜辛汤(苓、甘、五味、姜、辛)、小青龙汤(姜、桂、麻、芍、辛、半、五味、甘),它们都有干姜,干姜是治疗涎沫的主药。《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干姜还可通过减少肠道分泌物止泻,如《伤寒论》第163条:“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桂、术、参、草、干姜)”。第395条:“大病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第306条:“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赤石脂、粳米、干姜)”。第157条:“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第225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真武汤方后:“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一两”。
干姜调节免疫的作用虽尚缺乏确切证据,但临床所见,黄师以桂枝甘草干姜汤治疗肝硬化、甘草泻心汤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红斑狼疮等免疫相关性疾病确有疗效,个中奥秘,留待日后继续观察与研究。
四、地黄
黄师经验:从防己地黄汤、百合地黄汤、炙甘草汤证有“神”的症状到地黄安神。经方中用地黄共十首,其中有三首方用生地黄,仲景时未有熟地黄,生地黄即鲜地黄,干地黄即现今之生地黄。百合地黄汤(百合、鲜地黄汁)、防己地黄汤(防己、桂枝、防风、甘草、鲜地黄汁)、炙甘草汤(地、冬、麻仁、桂、姜、枣、草、参、胶),而三首方都有“神”方面的症状。可知鲜生地是滋阴补液、养心安神的要药,治疗有“神”方面症状的抑郁症效佳。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防己地黄汤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伤寒论》第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生地黄一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参与组方12方次,其中参与汤剂组方7方次,在这7个汤方中生地黄用量最大的是防己地黄汤,用了2斤,炙甘草汤中用了1斤,百合地黄汤中用了1升,其数量明显大于方中其他药物的用量。
影响到神志的疾病,如癫狂、郁病之类,多属病情复杂、治疗棘手的顽固病,这类病症,用王道之药、中庸之剂,多如隔靴搔痒,井深绳短,缓不济用。而重用生地黄治疗具有神志异常表现的疾病,往往可收迥然不同的意外疗效。
黄老以生地治疗神志异常的疾病时,多从45克开始,最大可用至120克,尝见黄师治卢姓老太婆中风后,嘴巴不自主嚼动,治卢姓老太双手躁动,都以防己地黄汤取得奇效。
五、半夏
黄师从《内经•邪客篇》半夏秫米汤覆杯则卧,悟到经方中用半夏治失眠。此方为《内经》仅有十方之一,专为不寐而设,为治疗不寐之方,功效显著。张景岳谓“治久病不寐者神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言半夏能除“目不得瞑”。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法半夏有良好的镇静神经中枢的作用。方中半夏的用量较大,可为常用量的4至6倍,常可用45~60克。
半夏剂如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半夏厚朴汤等方都有精神症状,如:心烦、惊、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喉中如有炙脔等。其中与半夏的作用关系很大。人但知半夏能降逆止呕、和胃祛痰,不知半夏能安眠。《灵枢•邪客》:治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吴鞠通很重视这个方,在《吴鞠通医案》中吴氏多案中运用本方,每重用一至二两,且其效颇显。如胁痛门•伊芳氏案:胁痛,但不成眠,用旋覆花汤合半夏秫米汤,用半夏一两。业已得寐,但未用半夏又彻夜不寐,酉刻再服《灵枢》半夏汤一帖。可见半夏确为安寐之品,黄师在临床上,每遇不寐患者,常重用半夏45克,甚至60克,效果颇佳。
随黄师学习2年余,目睹过数不胜数的成功案例,我也在临床上学习黄师运用经方治病,疗效大大提高。我在随师中,找到了作为中医的感觉和自信。经方者,经典方、经验方,所以应该是经常用的方和疗效满意的方。而方由药组成,仲景用药的规律,不可不究。在原著中探究经方的用药思路,付诸临床检验和实践,不断思考与总结,永远是我们研究经方的重要课題和方向。
(全书完)
我的老师黄仕沛对经方有着真挚而执著的感情,他始终以孺子之心,锲而不舍地研究、实践经方,从不沽名钓誉、空谈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临床疗效显著,屡起沉疴。最难能可贵的是,黄师把宝贵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使我等后学之辈得益匪浅。得遇名师指点,是我从医路上最大的幸运和收获。黄师向来主张回归仲景原意,用仲景思想诠释经方内涵,在原著中探求经方的用药思路。仲景之方,方精、药少、效佳、果验,故黄师反对随意加减经方。跟从黄师学习,令我体会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兴兵须有理,用药要有因。“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历代兵家常胜者,必善用兵;历代医家有名者,必善用药。故以黄师传授的部分仲景用药心法,作为随师体会的内容,以求抛砖引玉,举一反三。
一、芍药
张仲景运用芍药独具特点,黄师从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到黄芪建中汤治虚劳里急,悟芍药诸方治诸挛急、腹痛。能体现此思路的经方有:芍药甘草汤、桂枝汤、桂枝加芍药汤、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黄芩汤、四逆散、大柴胡汤、当归芍药散、小青龙汤、真武汤。
芍药一味,其“止痛”作用早有记载。如《神农本草经》称芍药可“止痛”,能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张仲景时代芍药无赤、白之分,黄师在临床上,取其缓急止痛功效时多用白芍,并且用量宜大,多在45克以上,甚至用到120克,方能获效。
仲景常用芍药配伍甘草治疗诸痉挛、痛证,芍药甘草汤即为代表方及基础方。世称群方之冠的桂枝汤就是以芍药甘草为基础方组合而成。黄师在临床上用芍药甘草汤治疗脚挛急、腰腿疼痛、下肢不能屈伸者,其脚即伸,效果立竿见影。临床所见,芍药甘草汤不仅可治疗肢体肌肉痉挛,还可治疗胃肠痉挛,如阵发性胃痛、腹痛、膈肌痉挛(如呃逆)、支气管痉挛(如哮喘)、子宫痉挛(如痛经、产后腹痛)、血管痉挛(血管痉挛性头痛)等,疗效显著。
桂枝加芍药汤,“本太阳,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方中芍药用量达六两,专为腹满痛而设。《伤寒论》中治“法当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中治“虚劳里急,诸不足”的黄芪建中汤,方中芍甘合用,缓急止痛,亦是此用。
黄芩汤是芍药甘草汤加黄芩、大枣,是治疗热利的名方,临床上,以此方治疗兼见腹痛的下利效果最佳。
《伤寒论》第318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四逆散中的芍药、甘草,正是治疗其腹中痛的要药。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治》:“妇人怀娠,腹中疞痛,当归芍药散主之”。本方中芍药用量最重,达1斤,黄老常以此方治疗妇人痛经、妊娠腹痛等疾病。
《伤寒论》第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痛,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黄师认为,小青龙汤中白芍的作用是缓解支气管痉挛,从而缓解咳、喘等症状克。
此外,真武汤中白芍的作用向来备有争议。以原文及仲景用药思路观之,在真武汤证中有“腹痛”与“肌肉瞤动”,故以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真武汤之芍药为“腹痛”与“肌肉瞤动”而设,非为利水而设。
需要指出的是,芍药治疗的疼痛,多是功能性疼痛,以阵发性、痉挛性疼痛效果最佳,对器质性疼痛疗效多不佳。此外,芍药用于缓急止痛时用量较大,根据仲景用药规律,胸闷、心悸者不宜。《伤寒论》第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后世多知炙甘草汤以桂枝汤为基础组成,黄师却认为乃桂枝去芍药汤组成,以芍药不利于胸满,悸者多满。而吴氏加减复脉汤以炙甘草汤去参、桂、大枣、姜,加入芍药。黄师认为大谬也。如此去桂枝却加芍药,断不能治“心中憺憺大动”的。
二、桂枝
桂枝在经方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仲景在《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使用桂枝的配方接近30%,桂枝汤更是群方之首。但临床上很多医生认为其“过于温热”而弃用。黄师深得仲景用桂之心法,临床运用得心应手。黄师从桂枝甘草汤证“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悟仲景悸证诸方必用桂。体现此规律的经方有:桂枝甘草汤、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炙甘草汤;苓桂术甘汤、苓桂味甘汤、苓桂甘枣汤、五苓散;桂枝甘草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伤寒论》第64条:“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本条是使用麻黄后汗出过多,导致动悸,以桂枝甘草汤治疗,可见桂枝可以定悸。在使用麻黄的经方中,大多配有桂枝甘草,以防止心悸的出现。如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等。本方为治心悸的基本方,含有此思路的经方还包括: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炙甘草汤;“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的桂枝去芍药汤等。桂枝不限于治疗心悸,还可治疗其他部位的悸动感,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桂枝不仅治疗心悸,还可治疗有“气上冲”感的疾病。临床所见,此种感觉也是心悸的另一表现形式,只是很多时候程度比心悸严重。体现此思路的经方包括:《伤寒论》第15条:“太阴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第121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枝二两也”(另见(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并治》)。第67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第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青龙汤已下,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主之”。
桂枝还可治疗因惊恐等因素引起的情志异常,而这些情志异常均可伴见惊悸。如《伤寒论》第118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乳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小品》云:虚弱浮热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故曰二加龙骨汤)。《伤寒论》第112条:“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第107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俑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临床所见,桂枝的平冲定悸作用不容置疑。黄师认为:后世但知枣仁、远志、柏子仁、龙眼肉,宁心安神治心悸,但弃桂枝治悸,甚为可惜。黄师治疗心悸时多用15克以上,治疗“气上冲”更大,可用至20克,甚至45克。张仲景时代并未细分桂枝与肉桂,随师所见,重症顽疾黄师多用肉桂,或者肉桂与桂枝同用,其余多用桂枝。随师所见治关老太婆奔豚,便是30克桂枝,与肉桂6克同用。
三、干姜
随师曾见黄师治一王姓妇人,支气管扩张病史多年,每晨必咯痰清稀盈碗,用甘草干姜汤合麦门冬汤治之收效甚显,可见干姜之用甚为微妙。干姜在经方中用得极为广泛,黄师运用干姜主要有二:一是虚寒性分泌物增多之证,如咳嗽泡沫痰、小便量多而清稀、腹泻水样便、呕吐痰涎等,“诸病水液,澄澈清冷”者皆可用之(“病痰饮者,当以药温之”是也)。二为治疗免疫相关性疾病,黄师根据临床经验提出干姜可能有调节免疫的功效。如以桂枝甘草干姜汤治疗肝硬化、甘草泻心汤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等。
黄师指出,经方遗尿之证有三:
一者《伤寒论》219条:白虎汤证之“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恻,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实为热闭神昏之遗尿。
二者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实则矢气,虚则遗尿,名曰气分”。
三者,便是甘草干姜汤了。此方可治疗遗尿,悟出肾着汤也可治遗尿,而治疗遗尿的主药是干姜(遗者,阳不敛阴也,膀胱括约肌失束也,机能低下也,温阳病自愈)。《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黄师曾以此方并控制饮食,治愈一孕妇糖尿、羊水过多,以其身重腰中冷、小便频为要点。
经方中治饮之方有:半夏干姜散(半、姜)、苓甘五味姜辛汤(苓、甘、五味、姜、辛)、小青龙汤(姜、桂、麻、芍、辛、半、五味、甘),它们都有干姜,干姜是治疗涎沫的主药。《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干姜还可通过减少肠道分泌物止泻,如《伤寒论》第163条:“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桂、术、参、草、干姜)”。第395条:“大病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第306条:“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赤石脂、粳米、干姜)”。第157条:“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第225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真武汤方后:“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一两”。
干姜调节免疫的作用虽尚缺乏确切证据,但临床所见,黄师以桂枝甘草干姜汤治疗肝硬化、甘草泻心汤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红斑狼疮等免疫相关性疾病确有疗效,个中奥秘,留待日后继续观察与研究。
四、地黄
黄师经验:从防己地黄汤、百合地黄汤、炙甘草汤证有“神”的症状到地黄安神。经方中用地黄共十首,其中有三首方用生地黄,仲景时未有熟地黄,生地黄即鲜地黄,干地黄即现今之生地黄。百合地黄汤(百合、鲜地黄汁)、防己地黄汤(防己、桂枝、防风、甘草、鲜地黄汁)、炙甘草汤(地、冬、麻仁、桂、姜、枣、草、参、胶),而三首方都有“神”方面的症状。可知鲜生地是滋阴补液、养心安神的要药,治疗有“神”方面症状的抑郁症效佳。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防己地黄汤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伤寒论》第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生地黄一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参与组方12方次,其中参与汤剂组方7方次,在这7个汤方中生地黄用量最大的是防己地黄汤,用了2斤,炙甘草汤中用了1斤,百合地黄汤中用了1升,其数量明显大于方中其他药物的用量。
影响到神志的疾病,如癫狂、郁病之类,多属病情复杂、治疗棘手的顽固病,这类病症,用王道之药、中庸之剂,多如隔靴搔痒,井深绳短,缓不济用。而重用生地黄治疗具有神志异常表现的疾病,往往可收迥然不同的意外疗效。
黄老以生地治疗神志异常的疾病时,多从45克开始,最大可用至120克,尝见黄师治卢姓老太婆中风后,嘴巴不自主嚼动,治卢姓老太双手躁动,都以防己地黄汤取得奇效。
五、半夏
黄师从《内经•邪客篇》半夏秫米汤覆杯则卧,悟到经方中用半夏治失眠。此方为《内经》仅有十方之一,专为不寐而设,为治疗不寐之方,功效显著。张景岳谓“治久病不寐者神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言半夏能除“目不得瞑”。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法半夏有良好的镇静神经中枢的作用。方中半夏的用量较大,可为常用量的4至6倍,常可用45~60克。
半夏剂如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半夏厚朴汤等方都有精神症状,如:心烦、惊、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喉中如有炙脔等。其中与半夏的作用关系很大。人但知半夏能降逆止呕、和胃祛痰,不知半夏能安眠。《灵枢•邪客》:治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吴鞠通很重视这个方,在《吴鞠通医案》中吴氏多案中运用本方,每重用一至二两,且其效颇显。如胁痛门•伊芳氏案:胁痛,但不成眠,用旋覆花汤合半夏秫米汤,用半夏一两。业已得寐,但未用半夏又彻夜不寐,酉刻再服《灵枢》半夏汤一帖。可见半夏确为安寐之品,黄师在临床上,每遇不寐患者,常重用半夏45克,甚至60克,效果颇佳。
随黄师学习2年余,目睹过数不胜数的成功案例,我也在临床上学习黄师运用经方治病,疗效大大提高。我在随师中,找到了作为中医的感觉和自信。经方者,经典方、经验方,所以应该是经常用的方和疗效满意的方。而方由药组成,仲景用药的规律,不可不究。在原著中探究经方的用药思路,付诸临床检验和实践,不断思考与总结,永远是我们研究经方的重要课題和方向。
(全书完)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客服
客服

扫码添加客服好友
 下载
下载

扫码下载
知源中医APP




 已在书架
已在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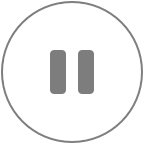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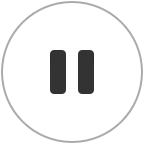













 方证相对医案
方证相对医案